編者按:每個人都渴望擁有完美人生,但往往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這樣的人生。所以當15年前《第二人生》以超前的理念誕生時,它一度被視為互聯網的未來,並在2007年達到了活躍用戶數過100萬的高峰。但此後隨着Facebook的崛起,《第二人生》的發展開始停滯,這是不是意味着人們更想要美化版的第一人生而不是虛擬的「完美的」第二人生?儘管如此,《第二人生》的月活用戶仍然穩定在80萬左右,而在這裡長期駐留的,是那些在現實人生中尋找不到慰藉的人:承受生活重負的家庭婦女,行動不便的殘疾人,生不了小孩的女子等等,《大西洋月刊》的這篇長文為我們講述了那些人的故事以及他們所打造的世界,從中我們可以看清楚虛擬生活的希望和限制,並且對虛擬和現實以及我們的人生也許還會有更加深刻的思考。
Gidge Uriza生活在一間高雅的木屋裡,透過巨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波光粼粼的小溪,岸邊垂柳依依,草地上螢火蟲閃爍如夢似幻。她不斷購買新的游泳池,因為她總是愛上了不一樣的泳池。現在的這個有着菱形圖案,還有瀑布從石拱門上流淌而下。Gidge會穿着泳衣在池畔露台閒逛,要麼就只穿着文胸和浴袍慵懶地縮進花邊的被子下躺着,身邊擺着一摞書,書上面堆放着巧克力蓋的甜甜圈。一天她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早上好,女孩。我動作緩慢,想要從床上爬起來,但當我躺在粉紅色的床上時,想要像往常一樣爬起來是有點困難的。」
在另外一種人生,也就是大多數人會稱之為「真實」的人生里,Gidge Uriza其實是Bridgette McNeal,一位亞特蘭大媽媽,每天要在在呼叫中心上8小時的班,還要撫養14歲的兒子和7歲的女兒,以及一對已經13歲的患有嚴重孤獨症的雙胞胎。她的現實生活完全被沒完沒了的照顧特殊需求的孩子的忘我和世俗所占據:在雙胞胎弄髒了自己之後要幫他們洗澡(他們仍然要穿紙尿褲,而且很有可能一直都要這樣下去),一邊烤蘋果醬麵包,一邊還得安撫其中一位發脾氣的,然後讓另一位不要再彈「《巴尼》主題曲了,因為那節奏慢得就像惡魔的輓歌一樣。」一天,她帶着所有的4個孩子去到一個自然中心享受一個田園牧歌式的午後,但這種美好一下子就被在一間發霉的浴室給一位少年更換紙尿褲的現實給打破了。
Bridgette McNeal,一位撫養着患有嚴重孤獨症的雙胞胎的亞特蘭大媽媽,她會在早上5:30醒來,在《第二人生》中度過一個半小時。

不過每天早上,在所有那些事情之前——在給孩子們做好上學準備以及到呼叫中心上8小時的班之前,在洗澡和癱倒在床上之前——Bridgette都會花上1個半鐘頭沉浸在《第二人生》這個在線平台裡面,那是她自己給自己打造的一個夢幻天堂。早上好女孩。我磨磨蹭蹭,艱難地想要從床上爬起來。她從早上5:30醒來,開始過上一段有着從來都不用下床的奢侈生活。
什麼是《第二人生》?簡短回答是這是2003年推出的一個虛擬世界,曾經被一些人歡呼為互聯網的未來。長一點的回答是,這是一幅布滿了哥特式城市、破敗得不像話的海濱棚屋、吸血鬼城堡、熱帶小島、雨林寺廟、恐龍家園、金光閃閃的迪廳夜總會以及超現實的巨大國際象棋遊戲的景觀地圖。2013年,為了慶祝《第二人生》的第10個生日,創造者林登實驗室發布了一張反映其發展情況的信息圖:3600萬賬戶,用戶在上面累計度過的年頭已經達到了217266年,居住在累計面積約7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而且還在不斷擴張。很多人忍不住把《第二人生》稱為遊戲,但在它推出2年後,林登實驗室給員工發出的一份備忘錄堅稱不應該這麼看待這個東西。它是一個平台。這句話的意思指向的是一個更加全面、更加沉浸式、更加包羅萬象的東西。
《第二人生》並沒有具體的目標。其巨大的景觀包含的全部都是用戶生成內容,也就意味着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由別人——由活生生的用戶控制的化身建設的。這些化身建設和購買房子,建立友誼,相互勾搭,組建家庭,以及賺錢。他們會慶祝自己的「rez日」,相當於網上的生日:他們加入《第二人生》的網上紀念日。在教堂,他們沒法舉行真正的聖餐儀式——把這種宗教儀式有形化是不可能——但他們可以把他們信仰的故事帶進生活。在他們主顯節島的大教堂,《第二人生》的聖公會在耶穌受難節會召喚滾雷,或者在復活節服務中當牧師念到「基督復活」的那一刻突然讓太陽升起。就像一本《第二人生》手冊概括那樣:「從你的視角來看,《第二人生》仿佛把你看作是上帝一樣。」
實際上,自從2000年代中期走下巔峰以來,《第二人生》已經逐漸淪為了笑柄。當我告訴朋友我在寫一則相關文章時,他們的面部總是呈現出相同的反應:先是茫然,然後似曾相識,接着是略為困惑的表情。那東西還在?《第二人生》已不再是你嘲笑的東西了,這些年來它已經變成你連取笑都懶得取笑了。
2007年,在月活用戶達到100萬之後,很多觀察家預計這個數字還會不斷上升,但結果那確實巔峰——並且在此後一直在80萬這個數字停滯不前。據估計20-30%的初次用戶此後從未回來過。在宣布《第二人生》是互聯網的未來的幾年後,技術世界是沉舟側畔千帆過。2011年,Slate的一篇文章加入了幡然醒悟的大合唱,宣告:「回顧過去,未來往往堅持不了不久。」
可如果《第二人生》應許的是一個大家每天都願意花數個小時生活的未來的話,難道我們不會深陷其中嗎?是,只是這種沉迷轉移到了Facebook、Instagram以及Twitter身上。隨着我對《第二人生》了解的深入,以及對它的探索投入了更多的時間,它看起來開始不那麼像是個被廢棄的遺蹟,而更像是我們當中許多人所生活的世界的被扭曲的鏡像。
也許《第二人生》讓人有嘲諷的衝動不是因為它的不為人所知,而是因為這種大家都看得出的衝動已經讓人感到不舒服,乃至於有點恐怖的地步:它不僅給你一個在線的聲音,而且還有一個在線的身體;不僅在你的手機上看Twitter消息,而且還因為你在一家網上俱樂部跳舞而忘了吃飯;不僅是你現實生活的精心策劃,而且還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存在。它同時喚起塞壬之歌以及想要另一種生活的羞恥之心。它提出了無拘無束的幻想能將人帶向何方,以及我們如何才能把握好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問題。
隨着虛擬現實技術的不斷發展,它有望帶來很多人認為《第二人生》可提供的體驗的更全面版本:完全沉浸在另一個世界裡。而隨着我們的現實世界每周不斷給我們帶來哪些驚悚——又一次大規模槍擊,又一次颶風,又一條來自美國總統威脅要發動核戰爭的推特——這個平行世界的吸引力只會進一步加強,而對我們自己沉迷其中究竟意味着什麼的懷疑也會進一步加深。
從2004年到2007年,人類學家Tom Boellstorff就以植入的人種志學者的身份生活在《第二人生》裡面,他的化身叫做Tom Bukowski,他還給自己安了一個家庭辦公室叫做Ethnographia。他的這張沉浸式的做法基於一個前提,那就是《第二人生》的世界就像任何其他世界一樣的「真實」,而他按照第二人生「自身的方式」而不是主要根據裡面那些人線下的生活去理解他們的虛擬身份去進行研究是合理的。他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第二人生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econd Life)》,這是對Margaret Mead的那本經典(《薩摩亞人的成年》)的致敬,探討了這個平台數字文化的本質。他發現「關於延遲(第二人生裡面的流媒體延遲)的小型討論就是像在現實生活中討論天氣一樣。」他還發現一位名為Wendy的化身,她的創造者總會在自己註銷前讓她去睡覺。「所以說現實的生活是Wendy的夢,直到她再度在第二人生中醒來?」 Boellstorff記得自己曾問過她:「我敢打賭Wendy在回答『是的,的確』時臉上掠過了一絲笑容。」
在印度教,化身的概念是指神以及凡人在地球上的化身。在第二人生中,它是你的身體——是你持續不斷的自我表現。一位女性是這麼向Boellstorff描述她的化身的:「如果我拉開拉鏈,把她的外殼取出來,裡面的就是我。」女性化身往往都是很苗條,而且胸大得離譜;男性化身都是年輕的肌肉男;幾乎所有化身都像卡通形象般好看。這些化身通過聊天窗口交流,或者利用語音技術進行實際的交談。他們通過走路、飛行、心靈傳動來移動,他們還會點擊「姿勢球」,這其實是一個漂浮的魔法球,點擊或者坐上去的時候化身就會做出各做動作:跳舞、空手道,以及幾乎你能想到的所有性行為。不要奇怪,很多用戶跑到第二人生來就是想尋找數字化性愛的可能性——沒有肉體、沒有真實姓名、沒有重力約束,往往有着詳細文字評論的性行為。
第二人生的貨幣是林登幣,最近它的匯率已經低到一林登幣不到半美分。在發行之後的10年時間裡,第二人生的用戶花了32億美元的真金白銀到平台內的交易中。第二人生的第一位百萬富翁,數字房地產大亨Anshe Chung(鍾安社)曾經登上了2006年《商業周刊》的封面,到2007年,第二人生的GDP甚至比好幾個小國的還要大。在龐大的數字市場裡,你可以用4000林登幣(16美元左右)買一件婚紗,或者用不到350林登幣(約1.5美元)買一件紅寶石顏色帶羽毛翅膀的緊身外套。你甚至可以再買一個身體:不一樣的皮膚,不一樣的頭髮,還可以有一對犄角,各種尺寸形狀的生殖器應有盡有。一座私人小島目前售價大約是150000林登幣(約600美元),而Millennium II Super Yacht超級遊艇售價為20000林登幣(僅80多美元),附贈的床上、按摩缸等的動畫超過了300個,旨在讓化身能盡情地進行各種各樣的性幻想。
Facebook開始爆發之日正是第二人生用戶數到達頂峰之時。Facebook的崛起與其說是競爭品牌的問題不如說是競爭模式的問題:似乎大家更想要的是一個精心策劃的真實生活而不是另一種全新的生活——他們想要成為自己最討人喜歡的形象超過了他們想要變成完全獨立的化身。不過也許Facebook和第二人生在吸引力方面其實差異並沒有那麼大。對於進入一個選擇性的自我來說,這兩個都表現出足夠的誘惑——無論這種自我是通過生活體驗的素材(露營的照片,對早午餐的機智觀察等)來打造,還是通過生活體驗所排斥的不可能性:一個理想的身體,一場理想的羅曼史以及一個理想的家來打造。
Bridgette McNeal,這位來自亞特蘭大的4個孩子的媽媽,她在第二人生上面呆的時間剛好超過了10年。她給自己的化身取名為Gidge,那是她上高中時那幫流氓給她起的外號。雖然Bridgette已經人近中年,但她的化身卻是20多歲的妙齡女子,她稱之為「完美的我——如果我不吃糖或者生小孩的話。」在第二人生的早期歲月里,Bridgette的丈夫也創建了自己的化身,在家坐在筆記本前學習時,兩人會一起跑到第二人生上面約會,一位金髮的古希臘女戰士跟一個矮胖的銀色機器人約會。這通常是他們唯一的約會方式,因為他們小孩的特殊需求使得找保姆很困難。我們交談的時候,Bridgette把她在第二人生的家說成是自己的庇護所。「當我步入那個空間時,我可以有自私的奢侈。」她借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話說:「那就好像是一間我自己的房間。」她虛擬的家布滿了各種各樣在她真正的家不可能有的東西,因為她的孩子可能會打碎或者吃掉那些東西——擺在碟子上的珠寶,桌上的小擺設,柜子上的化妝品。
Gidge Uriza ,Bridgette McNeal在第二人生裡面的化身
除了記錄其數字化存在,描寫大理石泳池和鑲邊松石綠比基尼的博客以外,Bridgette還堅持寫博客記錄她為人父母的日常生活。在那篇敘述自己跟孩子們在自然中心度過的那個下午的文章里,她描寫了自己看見一頭禿鷹的情形:「某個混蛋用一支箭射向這隻鷹。它的一隻翅膀幾乎都沒了所以沒辦法再飛了。我們到這兒的幾天前它剛剛被送到這裡養傷。有時候我在想我和我老公感覺有點像這隻鷹一樣。陷入困境。其實也沒出什麼問題,我們有吃的有住的,我們想要的東西都有。但我們的餘生都被困在孤獨症上面了。我們永遠也無法自由。」
當我問Bridgette第二人生有什麼誘惑時,她說當你應該關注現實生活時,往往很容易屈服於把自己投入到虛擬現實的誘惑當中。我問她這麼做的時候心裡有沒有打過鼓時,她說自己當然感受過一股拉力。「在裡面你又苗條又漂亮。沒人要你去換紙尿褲。但你會(因為現實的顧慮而)筋疲力盡。你不想離開,但同時你再也不想這麼幹了。」
第二人生的發明者叫做Philip Rosedale,他是一位美國海軍運輸機飛行員與一位英語教師的兒子。小時候,他就受到了有抱負所帶來的那種特別遠大的感覺的激勵。他還記得自己站在自己後院的柴堆旁思考人生:「為什麼我會在這裡?我跟其他人又有什麼不同?」1980年代中期十幾歲的時候,他用一台早期型號的PC對一個表示曼德布洛特集合的圖形進行放大縮小,這個無限遞歸的分形圖會隨着他靠得越近而呈現得愈發細緻。他告訴我說,後來他意識到自己在看着一幅比地球還要大的圖形:「我們哪怕在它表面走一輩子也看不完它的一切。」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意識到「用計算機可以做的最酷的一件事情是建造一個世界。」
第二人生的創造者Philip Rosedale往往會用名為Philip Linden的化身在虛擬世界裡面閒逛。他說:「我就像上帝一樣。」
1999年,Rosedale剛剛成立林登實驗室的時候,他去參加了火人節,這是在內華達沙漠舉辦的一個一年一度的行為藝術、雕塑裝置以及迷幻享樂主義的反傳統狂歡節。他告訴我,在那裡的時候,他的性格發生了「無法解釋」的改變。「就感覺自己很嗨,儘管沒有嗑藥。感覺自己跟別人以一種正常無法做到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他去到一輛清風房車參加一場銳舞活動,看着盪鞦韆演員在沙漠中搖曳,躺在鋪着好幾百波斯地毯的水煙館裡面。火人節並沒有啟發Rosedale去做《第二人生》——他對數字世界的設想已經進行了好些年了——但卻幫助他理解了他想要召喚的那種能量:一個大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創造世界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我們唯一的競爭對手是現實生活。
這是個夢想,但是推銷給早期投資者會比較困難。林登實驗室提出的是一個由愛好者打造的世界,並且用不同的收入模式來維持——不是靠付費訂閱,而是利用應用內產生的商務收入。第二人生的一位設計師回憶起投資者的質疑:「創意是一門黑暗藝術,只有斯皮爾伯格和盧克斯才能做得到。」為了把第二人生當做一個世界而不是一個遊戲來兜售,林登實驗室聘請了一位寫手充當「植入式記者」。這個人就是Wagner James Au,他在一個叫做「新世界筆記」的博客,然後在林登實驗室的聘用期結束之後,他寫了一本書《The Making of Second Life(第二人生創世記)》來記錄了第二人生早年的編年史。在這本書里,Au描寫了幾位對第二人生最重要的早期建設者:一個名為Spider Mandala的化身(線下的身份時美國中西部一個加油站的經理),另一個叫做Catherine Omega,在第二人生裡面是一位「淺黑膚色的女朋克」,但是在線下她卻蜷縮在溫哥華一棟被廢棄的公寓裡面,那裡沒有自來水,住的主要是癮君子,為了能在自己的筆記本上跑第二人生,她會用一個湯罐頭去捕捉附近辦公樓的無線信號。
Philip Linden,Philip Rosedale的化身
Rosedale向我講述了早年感覺到第二人生潛能無限時那種的興奮感。他和他的團隊在做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在做,他記得:「我們經常說我們唯一的競爭對手是現實生活。」他說2007年曾經有一段時間每天有超過500篇文章是描寫林登實驗室的工作的。Rosedale喜歡用一個叫做Philip Linden的化身去探索第二人生。他告訴我說:「我感覺自己我就像上帝一樣。」他設想將來他的孫子會把真實世界看成是某種「博物館或者劇院」,因為大部分工作和關係都是在類似第二人生這樣的虛擬現實中進行的。2007年他告訴Au說:「從某種程度來說,我認為我們將看到整個實體世界被拋到身後。」
Alice Krueger是在20歲的時候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疾病症狀。一次大學生物課野外作業期間,在蹲下觀察蟲子吃葉子時,她覺得熱得快暈過去了。有一次站在雜貨店時,她感覺自己的整條左腿都消失了——不僅僅是麻木,而是消失了的感覺。可是每次去看醫生的時候,她都被告知這只是她腦子裡的想法。47年後,她告訴我說:「這種想法一直在我腦海里占據着。不過跟一般的理解不一樣。」
Alice Krueger喜歡找滑道玩——她很享受做她的身體無法做到的事情所產生的那種絕對的興奮感。
50歲的時候Alice終於被診斷為多發性硬化症。那時候她幾乎都已經不能走路了。社區協會不同意她在自己的屋子前面建一個斜坡,所以她想去哪裡都很困難。她的3個孩子分別是11、13和15歲。她沒法出席自己最小兒子的中學畢業,也去不了他的大學校園。她的後腰開始感覺到劇痛,最終被迫進行手術來修復融為一體的腰椎,後來在醫院的時候又被多重耐藥性葡萄球菌感染。她的疼痛一直在持續,後來又被診斷因為一次手術原因而導致錯位——在那次手術中,她「就像烤雞一樣」被掛在手術台之上。57歲時,Alice出不了門也沒有工作,身體經常遭受劇痛,基本上要靠女兒照顧。她告訴我說:「我看着四周的牆在想,也許還有更多的牆。」
患有多發性硬化症的Alice Krueger創建了一個叫做Gentle Heron的化身,並且在第二人生為殘疾人建立了一個社區。
就在這個時候她發現了第二人生。她創建了一個叫做Gentle Heron的化身,並且喜歡尋找滑水道去玩——她很享受做她的身體無法做到的事情所產生的那種絕對的興奮感。在第二人生裡面不斷探索的同時,她還開始邀請網上遇到的殘疾人進聊天室跟她一起聊。但這同時也意味着她要對那些人的經歷負責任,最終她在跌人生成立了一個「跨殘疾人虛擬社區」。這個社區現在的名字叫做「Virtual Ability」,他們占據了虛擬島嶼的一個群島,並且歡迎從唐氏綜合徵、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到躁狂症等各種殘疾人的進駐。Alice告訴我說,讓這群會員團結在一起的,是那種不被這個世界充分接納的感覺。
在創辦Virtual Ability的同時,Alice在現實生活中也開始行動:從科羅拉多搬到田納西州的斯莫基山,在那裡她的長期傷殘補貼能夠用得更久。在被問到是不是感覺在第二人生裡面是一個不同版本的自己時,她強烈地駁斥了這種說法。Alice很不喜歡真實和虛擬的說法。在她看來,這暗示了一種等級差別,潛台詞時她的一部分生活要比另一種更加「真實」,但她的自我感在這兩種生活裡面都得到了一樣的充分表達。在我們第一次交談之後,她給我發了15篇經同行評審的有關數字化身的科學文章。她不希望第二人生被誤解為無關緊要的消遣。
Gentle Heron,Alice Krueger的化身
Alice告訴我一個患有唐氏綜合徵的男子後來成為了Virtual Ability社區的重要成員。在現實生活里,他的無能力似乎無所不在,但在第二人生里大家跟他交流的時候甚至都沒意識到他是唐氏患者。在線下世界,他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居然能控制自己的化身,父母都感到很驚訝。每天晚飯過後,父母在洗碗洗碟的時候,他就會熱切地坐在計算機旁,等待着回到第二人生裡面,他在一座叫做Cape Heron的島嶼(這是Virtual Ability群島的一部分)租了一套複式住宅。他已經把二樓一整層都變成了一個龐大的水族館,這樣他就可以跟魚兒一起走了,一樓則被改造成了花園,他在裡面養了一頭寵物馴鹿,還餵給它麥圈吃。Alice說他並沒有給第二人生和「現實」之間劃清明確的界限,社區的很多人也都受到了他的這張做法的啟發,在談到自己腦海中這道邊界的坍塌時總是會提到他。
我開始構思這篇文章時,曾經想象過成為第二人生的奴隸:一位睜大眼睛的觀察者會受到她所要分析的文化的誘惑。但是身處這個「世界」里卻讓讓我從一開始就感到反胃。我設想我會像它曾被認為不過是「第一人生」不盡如人意時的安慰獎那樣替第二人生辯護。但相反的是,我發現我想要寫的是「第二人生讓我想要洗個澡冷靜一下」。
從理智上來說,當我聽說了一位中東的女性可以不戴頭巾穿越到第二人生時,當我跟一位替身有個露台她可以用那個視角(這要感謝屏幕放大軟件)以比現實世界更清晰的角度去瀏覽的法定失明的女性交談時,我對它的尊敬都會進一步加深。我還聽說有位得了PTSD的老兵每兩周都會在一個露台舉辦意大利烹飪課,我還參觀了一個在線版的優勝美地,那是一位女性在幾次嚴重的抑鬱發作並且住院治療後加入了第二人生並且創建出來的。她用了一個叫做Jadyn Firehawk的化身,並且一天有12小時都泡在第二人生裡面,其中有很多時間都是用來完善她定做的仙境——一個到處都是瀑布、紅杉以及用對約翰·繆爾一生很重要的人士命名的馬匹的地方。要感謝第二人生,不像專注於躁狂症,討論的都是疾病的互聯網聊天室,這裡對她沒有這些要求。她告訴我說:「我在第二人生過着一種全面的生活。它接納了所有其他不同的我。」
一位女性創建了虛擬版的優勝美地,以及以對約翰·繆爾一生很重要的人士命名的馬匹。
但是儘管我對它越來越欣賞,儘管我沉醉在魔法的幻想,但是總止不住對第二人生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厭惡——對那些畫面的空虛,對那些夜總會、大廈、泳池和城堡,以及對他們拒絕讓這個世界感覺像是個世界的所有那些勇氣和不完美的厭惡。每當我想描述第二人生時,我都會發現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不可能描述得很有趣的——因為不管怎麼描述總會找到瑕疵和缺陷,而且探索第二人生的世界更像是瀏覽一張張的明信片。第二人生是視覺上的老套世界。這裡沒有一樣東西是破爛或者荒廢的——就算有廢棄的,那也是因為他們從預設的一系列選擇中選擇了特定的美學風格。
當然,我對第二人生的厭惡——以及我對物理世界的瑕疵和不完美的接受,這些都說明了我自己的運氣不錯。當我在現實世界走過時,我有我的(相對)年輕、(相對)健康以及(相對)自由作為緩衝。那些在第二人生裡面找到了自己在線下找不到的東西的人又有誰值得我羨慕的呢?
一天,當我和Alice都用化身見面時,她帶我去到Virtual Ability島嶼的一個小島的海灘並且邀請我練太極。我只需要點擊漂浮在草綠色圓圈中間的一個姿勢球,然後它就會自動讓我的化身動起來。但是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打太極。我只感覺到自己坐在筆記本前,看着我的二維化身打太極。
我想起了亞特蘭大的Bridgette,她會早早醒來坐在虛擬泳池邊。她聞不到氯氣或者防曬油,感受不到太陽在她後背熔化或者把她的皮膚烤成剝落的薯片。儘管如此,Bridgette作者虛擬泳池旁一定是得到某種強大的東西——一種不是來自於肉體體驗本身,而是來自於期盼、記錄、回憶,以及與其每天背負的責任形成鮮明對照的快樂。否則的話她是不會在早上5:30爬起來做這件事情的。
從第一開始我就不擅長駕馭第二人生。我的界面反覆在說身體下載不了。第二人生本來是要給你機會去完善你的身體的,但我甚至連湊齊一個完整的身體都做不到。我給自己的化身選擇了一個朋克造型的女性,她身穿短褲,理了個寸頭,肩膀上還站着一隻雪貂。
我在第二人生的第一天就像個醉鬼一樣在Orientation Island上亂走亂逛想要找個衛生間。這個島到處都是大理石柱和裁剪過的綠色植物,隱隱能聽到流水潺潺,但它看起來不那麼像德爾菲神廟而更像是受到德爾菲神廟啟發的企業療養中心。圖形似乎不完整也沒什麼吸引力,動畫小問題不斷而且總是有延遲。這不是現實的勇氣和掙扎;這更像是一個腳手架東倒西歪搭設出來的舞台。我曾經試着跟一個叫做Del Agnos的人聊,但令人吃驚的是他斷然回絕了,這很令我羞愧,仿佛被帶回了羞怯到令人失去勇氣的初中年代。
我第一次參加第二人生音樂會時興奮地聽到了一個在虛擬世界裡演繹的真實音樂:很多第二人生的音樂會都是如假包換的「現場」演出,有真正的音樂家用真正的樂器演奏真正的音樂或者對着連上計算機的麥克風唱歌。但是那個下午我同時想做的事情太多了:16封工作郵件等着我回復,我的繼女排演《彼得潘》之前要給她準備花生醬果凍三明治。我用黏糊糊的手指點了一下跳舞姿勢球然後開始跳康茄舞——尷尬的是沒人跟我一起跳;這讓我陷在了一株盆栽植物與舞台之間,想要跳康茄但又無處可去。這種超過任何有趣感的窘迫,倒是讓我有了涉入感,意識到我是在跟別人一起分享這個世界。
第二人生不會自己打開大門……它會向你展現一個世界,讓你用自己的設備去探索
每次我退出第二人生的時候,我都很渴望投入到日常生活,重新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接繼女去上戲劇班?搞定!回復系主任招人替代意外離開的系成員的事情?在辦!這些責任帶給人的真實感是第二人生所無法提供的,它們讓我活出了一個有能力、被需要的自我。這感覺就像是在水下無法呼吸之後終於掙扎着浮出了水面一樣。我大口地喘氣,不顧一切想要那些糾葛與牽連,我想要說:是的!這就是真實的世界!
作者給自己創建的化身
當我採訪Philip Rosedale的時候,他大方地承認第二人生一直都帶給用戶固有的困難——用戶想要舒服地移動、溝通和建造很難;「鼠標和鍵盤相關的不可緩解的困難」導致玩第二人生「永遠沒法變簡單」。林登實驗室負責全球溝通的資深總監Peter Gray向我講述了所謂的「白區問題」——由於自由度太高以至於你沒法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並且承認進入第二人生會像是「被扔進了異國他鄉的腹地。」
不過,當我跟用戶交流時,第二人生執拗的不方便似乎已經成為了他們以第二人生居民的身份講述內容的關鍵部分。他們以懷舊的口吻來回顧早年的窘迫。Gidge告訴我有一次有人說服她需要買一個陰道,後來她把那玩意兒戴在了褲子外面。(她稱之為典型的# SecondLifeProblem。)Malin sth,一位瑞典音樂家,也是那場音樂會的表演者之一,告訴了我她出席第一次第二人生音樂會的經歷,她的故事跟我的差異並不大:當她試圖走到大家面前時,卻意外飛上了舞台。事先她本來已經在內心確定了這整件事就是假的,但是卻對自己感覺之羞愧感到驚訝,這讓她意識到其實自己是覺得自己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我知道她的意思。如果我感覺像是回到了初中的話,那至少你也會感覺像是出現在哪裡。
一位女性是這樣總結的:「第二人生不會敞開自己。它不會輕易地交給你任何東西,告訴你下一步該去哪裡。它向你展現了一個世界,讓你用自己的設備去探索,這裡不歡迎指導。」但一旦你搞清楚之後,只要你想就可以買1000個銀盤——或者買下你夢想的遊艇,或者建設一個虛擬的優勝美地。Rosedale相信如果用戶能夠熬得過最初的煉獄,則他們與第二人生的關係就將永遠確立:「如果他們呆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就再也不會離開。」
Neal Stephenson1992年的網絡朋克小說《雪崩》描寫了一個虛擬的「Metaverse(虛擬空間)」,這往往說成是第二人生主要的文學始祖。但是Rosedale向我保證,他讀到這本書的時候第二人生已經構思了好幾年了(「你可以去問問我妻子。」)。《雪崩》裡面的英雄有一個很適合的名字,叫做Hiro Protagonist,在現實生活里他跟室友住在U-Stor-It貨櫃裡,但在Metaverse裡面他卻是舞劍的王子和傳奇黑客。他在上面花了那麼多時間並不奇怪:「這可以擊退住在U-Stor-It里的挫敗感。」
Hiro的雙重人生get到了第二人生的核心夢想之一:它可以顛覆現實世界成功的所有指標,或者讓那些指標變得一文不值;它可以建立一個極其民主的空間,因為沒人知道別人在真實世界的地位。許多第二人生的居民把它理解為一個連接全世界的人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跨越了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職業、不同地方、不同殘疾程度的人,讓生病的人擁有健全的身體,行動不便的人可以自由的遷移。Seraphina Brennan,一位在賓夕法尼亞一個小礦區長大的變性人直到20多歲以前都沒法承擔變性手術的費用,她告訴我說第二人生給了她「以內心真正想要的面目出現的機會,」因為這是第一個她能以女性身體示人的地方。
在《The Making of Second Life》中,Wagner James Au講了一個叫做Bel Muse的化身的故事,這是一位典型的「加州金髮女郎」,由一位非洲裔美國女性扮演。她領導了一支早期建設者團隊建設Nexus Prime,這是第二人生地首批城市之一,並且告訴Au這是她第一次沒有遇到已經習以為常的成見。在真實世界裡,她說:「我必須馬上給人留下好印象——我必須有好表現,馬上。在第二人生里我不需要了。因為哪怕有那麼一次,我就會離開。」但是這件事——Bel Muse被當作白人是更容易受到尊重——反而更加確認了種族主義的頑固而不是為擺脫這種歧視提供了證據。
很多第二人生的用戶視之為提供了一個公平的競技場,認為這裡擺脫了階層與種族的束縛,但裡面身材苗條的白人占優勢,大多配備了有閒階級的道具,這些只不過是把被扭曲的同樣的理想,以及一樣的把「白色」作為無形的默認又重述了一次,這從一開始就支撐着一個不公平的競技場。
另一位非洲裔美國女性Sara Skinner倒是一直都讓她的化身擁有跟她一樣的膚色,她告訴我說她想要在一個叫做Bay City的海濱城市建一座數字化的黑人歷史博物館。另一個化身(扮演警察)馬上豎起了一道牆,而且最終一家「法院」還禁止該博物館顯示出來。那位警察化身宣稱這是一個誤會,但拒絕承認有此行為的種族主義太多了——而且當Sara拒絕了第二人生裡面的一位白人男性的建議之後對方馬上說她長得像靈長類動物時,或者有人因為她的鼻孔很大而取笑成「棉塞鼻子」時,或者當比人告訴她感受到的偏見時不成立的,因為她是個「混種」時,這絕對不是什麼誤會。
Au告訴我起初他對第二人生的前提,尤其是用戶生成內容的可能性是極其感到興奮的,但結果發現大多數人對突破自身創意潛能的興趣其實不比成為一個年輕性感有錢的世界的消費者的興致。Rosedale告訴我他以為第二人生的景觀會是超級夢想、富有藝術性並且極其瘋狂,到處是宇宙飛船和奇特地貌,但結果出來的看起來更像是馬里布(加州地名)。大家都在造高樓大廈和法拉利。他告訴我:「我們一開始是在一個大家最垂涎的地方去建設。」他提到了林登實驗室早期進行過的一項研究,結果發現第二人生絕大部分的用戶在現實生活中都是住在郊區而不是市區。他們來到第二人生是想尋找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缺少的東西:都市地區的集中、密度以及連接的可能性;那種事情在自己周邊發生的感覺;那種成為所發生的事情的一部分的可能性。
Jonas Tancred 加入了第二人生的時間是2007年,那是在他的企業獵頭公司在衰退期間倒閉了之後。Jonas住在瑞典,他已經人近中年頭髮發白大腹便便,而他的替身Bara Jonson,卻是個年輕的肌肉男,長着刺頭活力四射。但是第二人生最吸引Jonas的不是讓他能扮演更有魅力的另一個自我,而是第二人生讓他有機會玩音樂,這是他從來都沒有追求過的畢生夢想。(他最終會跟Malin sth組建二人組Bara Jonson and Free)Jonas開始舉辦虛擬演奏會。在現實生活中他會站在蓋上格子布的餐桌前,彈奏接上計算機的民謠吉他,而在第二人生裡面Bara會在一群人面前玩搖滾。
Jonas Tancred和Malin sth在第二人生組建了一支流行樂隊叫做Bara Jonson and Free
一天晚上,在演出之前,一位女性過來跟他打招呼。他在她面前進行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演奏之一。那位女性叫做Nickel Borrelly;她將成為他(在第二人生中)的妻子,並且最終在幾年之後,成為了他(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媽媽。
在線下,Nickel是一位生活在密蘇里叫做Susie的年輕女性。經過一場超現實的求愛——熱氣球之旅,浪漫的月光下共舞,以及在長城一起騎自行車之後,「SLT(標準林登時間)時間凌晨12點」,兩人在Twin Hearts Island舉行了一場第二人生婚禮。在婚誓中,Bara說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不過他說的一生究竟是哪一個人生呢?
Bara在第二人生的音樂生涯開始騰飛,最終他得到了到紐約去錄製唱片的機會,這是第二人生的音樂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拿到了唱片合約。也正是在那次旅行中Jonas第一次在真實世界裡見到了Susie。幾年後,當他們的關係被拍成了紀錄片時,她描述了自己的第一印象:啊,他看起來有點老啊。不過她說得以親自見到他本人感覺就像「第二次墜入愛河」一樣。後來她時怎麼懷孕上的呢?她在紀錄片裡說:「我可以告訴你是怎麼發生的。喝了很多伏特加之後。」
2009年,Susie和Jonas的兒子Arvid出生了。(Susie和Arvid都改過名)那時候,Jonas已經返回瑞典,因為簽證到期了。Susie在產房的時候,他在第二人生的俱樂部里——一開始是等消息,然後是抽一根虛擬雪茄。對於Susie來說,最困難的是Arvid出生後那天,醫院裡擠滿了來看自己孩子的其他父親。SUSIE和Jonas能做什麼呢?到海邊的一個浪漫飛地一起煮一頓虛擬的早餐,舉着已被不能喝的熱氣騰騰的咖啡,靠在虛擬沙發上的時候一起在虛擬電視上看着他們真正的孩子的真實視頻。
Susie和Jonas不再墜入愛河,但Jonas仍然是Arvid生活的一部分,他們頻繁地視頻通話,並且只要有機會就會去美國。Jonas相信在分開後他跟Susie仍然能維繫牢固的育兒關係,原因之一是他們在現實生活中見面之前已經在網上非常深入地了解了彼此——第二人生不是一個幻覺,而是能比真實生活的求愛期更好地了解彼此的管道。
Jonas說第二人生是現實的純化版,而不是其膚淺的替代。作為一名音樂人,他覺得第二人生並沒有改變他的音樂,而是「放大」了它,使得他跟自己的觀眾有了更直接的聯繫,他很喜歡粉絲能夠自己給他的歌賦詞的方式。他記得自己在翻唱Crash Test Dummies樂隊的《Mmm Mmm Mmm Mmm》時,每個人「一起跟唱」的情形,敲歌詞的人太多以至於到最後他們的「mmm」把整個屏幕都占滿了。對於Jonas來說,現實與他的創造——那些歌以及他的孩子的美已經超越和勝過了他們的虛擬建構。
在3600萬第二人生的賬號(截止2013年,這是林登實驗室提供的最近數據)裡面,據估計只有60萬人仍經常使用該平台。也就是說大量用戶離開了。究竟發生了什麼?
Au把Facebook的崛起與第二人生用戶數走到高原期的同時發生看作是林登實驗室誤解了公眾想要什麼的證據。Au告訴我說:「第二人生推出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想要第二種人生,但市場證明並非如此。」
但當我跟林登實驗室全球溝通總監Peter Gray以及產品副總裁Bjorn Laurin交談時,他們堅稱問題不在於概念,而在於完美執行的挑戰。他們告訴我,用戶達到穩定恰恰證明了界面的難度,而且事實上技術業還沒有取得足夠的進展,實現媒體炒作的第二人生可能會實現的效果:一個完全沉浸式的虛擬世界。他們希望虛擬現實能夠改變這一點。
Rosedale預測有朝一日我們會把真實世界看作是「古老而可愛的地方」——但不再至關重要。
去年7月,林登實驗室推出了新平台Sansar的beta版,稱這是下一個前沿:一個針對Oculus Rift這樣的虛擬現實頭戴設備的3D世界。該公司的信念,以及VR在技術界的受歡迎程度(Facebook收購Oculus VR所證明的一股趨勢),提出來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虛擬現實的進展解決了笨拙界面的問題的話,它們會不會最終透露一個普遍的渴望,也就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那些小故障、延遲和鍵盤所解放出來的虛擬世界?
2008年,Rosedale不再擔任林登實驗室CEO。他告訴我他認為自己更像是一位發明家,而且他覺得公司需要一位更好的經理。他對第二人生變成現在這樣並不感到失望,但他也看到了其他未來可能性的出現:在虛擬現實成熟之後,他就能「建造星球和建設新經濟」了。他目前的公司High Fidelity正在致力於開發沉浸式的VR技術,能沉浸到感覺自己跟別人共處一室的那種。
Au告訴我他注意到技術界總是很狂妄。他們不是從錯誤中學習,而是一再重複做同樣的事情。第二人生的故事是不是一個技術界妄想的固執?還是說這種妄想更像是一種預言?第二人生是不是我們數字化存在未來有先見之明的先驅?
當我問Rosedale現在還相不相信自己在第二人生早年做出的預測——也就是我們的生活會變成虛擬,物理世界將開始像博物館時,他並沒有改變想法。恰恰相反:他說到了一定時候我們會把真實世界看作是「古老、可愛的地方」,而不再是至關重要。他在想:「當我們不再需要辦公室時我們會如何處置它們呢?會不會在裡面玩壁球呢?」
我進一步追問他。他是不是真的以為物理世界的特定部分——比方說,我們家人一起分享的家,或者我們跟朋友一起吃的飯,我們緊緊依偎在一起的身體——有朝一日會變得不再重要?他真的相信我們的肉身對我們的人性不重要嗎?我對他承認之快感到驚訝。他說,家庭——實體的家,我們選擇跟所愛的人共度時光的地方的氛圍永遠不會過時。「這是一個更加持久的存在。我想你也同意這一點。」
Alicia Chenaux住在一個叫做Bluebonnet的小島,那是一個草木叢生的古怪飛地。跟她住在一起的還有跟她的丈夫Aldwyn(Al),兩人結婚已有6年,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8歲的Abby以及3歲的Brianna,儘管過去她曾經是5歲,再之前曾經是8歲。作為一個家庭,他們每天過着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往往作為數字快照被截圖到Alicia的博客上:在南瓜地尋找做南瓜燈的材料,在像素化的大海去希臘游幾天的泳。這就像一幅數字化的諾曼·洛克威爾油畫,一種典型的美國中上階級生活——一個完全不值得注意的幻想,除了Abby和Brianna都是由成人扮演的化身以外。
當Alicia在30出頭發現自己要不了小孩時,她陷入了長時間的抑鬱之中。但是第二人生給了她為人父母的機會。她的虛擬女兒Abby在真實生活中8歲時受到了嚴重的創傷(具體細節Alicia覺得沒有必要知道),所以她扮演這個年紀讓她有機會過的更好。在現實生活里Brianna Brianna是由保姆撫養的——她的父母不怎麼管她的養育——而她希望成為家庭的一部分,從而能夠得到更多育兒的親身實踐。也許這就是她總想變年輕的原因。
Alicia Chenaux是一位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要小孩的女性化身。在第二人生中她跟丈夫Al以及女兒Abby和Brianna生活在一起。
Alicia和她的家庭是第二人生一個更大的家庭角色扮演社區的一部分,收養機構會接收孩子和潛在父母的檔案,並對他們進行「考驗」,讓雙方住在一起一段時間,看看是不是合得來。本該是第二人生黑人史博物館創始人的Sara Skinner告訴我撫養4歲兒子(由一位在美軍服役被派往海外的男人扮演)的經歷:他的連接經常斷斷續續,只是為了跟Sara閒逛幾個小時。
有時候領養父母要進行虛擬懷孕,利用「出生診所」或者叫做「tummy talkers」的附件——這種東西提供了你需要的一切:預產期、身體改造(均可調整),可選擇胎兒發育是否可見;詳細的公告(「你的孩子翻身了!」);』以及「真實分娩」的模擬,還有一個新生嬰兒的附件。對於認養後經歷過懷孕過程的第二人生父母來說,他們得到的這個小孩正是他們領養的那位是很好理解的——這個過程本來就是為了讓父母和孩子跟一個新生命結成紐帶。一個產品承諾:「真的會有孕吐反應。會有疼痛感。」意思是告訴你一個不是你的肉身的軀體正在有噁心反應。這款產品還推銷說:「你可以完全控制你的懷孕,讓它完全按照你的期望。」我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好已經懷孕了6個月,在我看來這似乎錯過了這一體驗的核心:其實事情恰恰不會按照你的意願發展,而是你需要忍受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過程。
在現實生活中,Alicia跟男友生活在一起,我問他是否知道她的第二人生家庭時,她說:「當然」。保守這個秘密會很困難,因為她幾乎每天晚上(除了周三,周三是她所謂的「真實生活之夜」,她會跟最好的朋友一起看真人秀。)都要跟他們3個在第二人生裡面溜達。當我問Alicia是否從她的這兩種浪漫關係中看到不同的東西時,她說,「絕對的」。她的男友非常好但是整天都要工作;Al願意聽她沒完沒了地嘮叨自己的日常。她和Al在結婚前已經相識了2年(她說主要是他的「耐心和毅力」吸引了她),她承認對於他們浩大的第二人生婚禮自己是個「徹底的控制狂」。在現實生活中,扮演Al的那個人年紀比Alicia要大——51歲,她39歲,也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她欣賞的是「他人生經驗豐富」以及可以提供「更保守、更穩重」的看法。
在他們的第二人生婚禮之後,每個人都開始問Alicia和Al是否打算要小孩。(這件事無論在虛擬世界還是現實世界都不會變。)4年前他們認養了Abby,並在1年後認養了Brianna,這段時間他們的家庭生活動態是在角色扮演與現實之間交織。當Brianna加入他們家庭時,她說她想要的「不僅僅只是故事」,有時候這個女孩會打斷角色扮演去講講自己真正的成人生活:感情麻煩或者工作壓力。但對Alicia來說重要的是她的兩個女兒都是「忠實的孩子」,意思是說她們沒有替代的成人化身。儘管Alicia和Al彼此會分享真實生活當中的相片,Alicia告訴我,「女孩們一般都不會分享自己的照片,她們更願意在我們的腦海里保留孩子的形象。」
Alicia的第二人生家庭有一點特別美好,那就是所有四個人都想生活在同一個夢想裡面。
2015年聖誕節的時候,Al給了Alicia一個「pose stand」,這讓她可以為家庭定製和保存姿勢:她和Al在一張長凳上擁抱,或者他讓她騎在肩上。Alicia很多博客發的都是一張一家人其樂融融的照片,往往在底部還有一條備註。其中一條是這麼寫的:「順便說一句,如果你想買本圖中我使用的姿勢,我已經把它放到Marketplace上面了。」在一篇文章中,在一張她和Al穿着舒適的冬裝依偎着坐在長凳上,周圍是積雪覆蓋的樹木的照片下方,她承認這是她在Al上床之後拍的照片。她用他的化身登錄進去然後讓他擺出了自己想要的姿勢。
在我看來,擺姿勢正好同時說明了第二人生家庭角色扮演的吸引力和局限性:它既可以不斷地被雕刻成某種田園牧歌式的東西,但你無意雕刻的東西永遠也刻畫不出來。儘管Alicia的家庭生活看似完美無缺——處處可見高光時刻——但正如Alicia告訴我那樣,其深層次的愉悅似乎卻來自那些困難的時候:當她被迫阻止女孩們爭執衣服問題或者度假回來發脾氣時。在一篇博客文章中,Alicia承認每天晚上跟Al獨處的「那幾分鐘」是她的最愛,但即便引發的這種經濟稀缺性——因為責任和犧牲所以顯得那些時光的寶貴——感覺也像是來自真實世界養育兒女的又一個姿勢。
去年,Alicia和Al又領養了兩個孩子,但是後來發現問題了,因為新領養的小孩想要的「太多了,太快了。」他們馬上就想叫Alicia媽、叫Al爹,並且從一開始就說「我如此愛你」了。他們渴望強烈的、不折不扣的養育,而不是間或的角色扮演,並且不斷做要求關注的事情,比如鞋子不見啦,從屋頂跳下來啦,爬上樹又下不來啦,或者做自己完成不了的項目等等。這麼說吧,他們的行為就像真正的小孩一樣,而不是成人的角色扮演。這次領養僅維持了5個月。Alicia的第二人生家庭特別美好的一點是所有4個人都想活在同一個夢想裡面。Alicia和她的孩子打造自己的親密關係的方式其意義是不可否認的,因為他們在現實中得不到周圍的承認。但他們階段性的摩擦(口角、關係惡化)也說明了他們這種完美家庭的幽閉恐懼症。也許第二人生家庭實現理想家庭生活的過程來得太簡單太高效,繞開了家庭生活太多的困難了。你的虛擬家庭永遠也無法完全超越你最瘋狂的想象,因為它只能建立在你能想象的基礎之上。
在我剛開始探索第二人生期間的一天晚上,我和丈夫一起站在下曼哈頓的一家燒烤酒吧(線下)外面,我問他:「為什麼第二人生就不能跟『真實生活』一樣真實呢?」他伸手過來掐着我的手臂說:「這就是為什麼它那麼那麼真的原因。」
他所指的不僅僅是肉體性——也就是我們的體驗受限於我們的身體——也包括意外和顛覆。我們的生活體驗有太多是由超出我們的中介和預測,超出我們的掌握,超出我們的想象的東西構成的了。在第二人生的完美景觀裡面,我總是會想起一位朋友告訴我他被關禁閉的體驗:剝奪他的自由不僅意味着沒法獲得這個世界所有可能帶來的快樂,也意味着不可能犯所有可能會犯的錯誤了。也許一個完美世界,或者一個表面上你能控制一切的世界的代價是,我們很多「體驗」都來自於我們自己沒法鍛造,以及最終無法放棄的東西。當然,Alice和Bridgette已經知道了這個,她們每天都靠這個生活。
原文鏈接:
編譯組出品。郝鵬程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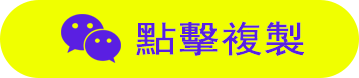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最近了解了一下,是我朋友給我推薦的,很靠譜,推薦大家情感有問題的可以嘗試一下
如果發信息,對方就是不回復,還不刪微信怎麼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