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19開放麥系列最後1篇
明年再會
2019年的中國電影,聲勢始終奪人,反響不絕於耳。
電影的主體性姿態從未如此挺拔昭著,我們對電影的聚焦也從未如此目光灼灼。

這一年,全國電影票房超過640億,銀幕數量逼近7萬塊,全年總計生產電影1037部。它穩居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小跑奔向世界第一大電影票倉。
這一年,華語電影從年初的春節檔,中經暑期檔和國慶檔,直至年末的賀歲檔,一路不可阻擋。
最終用47部破億影片和全年票房前10名豪取8席的赫赫戰績,叫響了名號,擦亮了招牌,為中國電影的固化形象添加了活性劑。
讓我們看到了中國電影表達的更多可能性,也看到了電影裡的中國式表達更具親合力的範式輸出。
這一年,中國電影人將「干就完了」四個字貫徹到底。
搶工搶時搶指標,像一支訓練有素的施工隊,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讓我們曾經以為不可抵達之處,開始水草豐茂,開始人山人海。
有關部門為之持續提供補給:中央級電影專項資金髮力助推藝術電影發行和電影的海外推廣,延期放映密鑰一次次助燃優秀國產電影的票房噴射裝置。
過去的一年,中國電影開墾了不毛之地,肥沃了處女地,也曾勇闖禁地。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比以往更為堅實地站在了這片土地。
審視2019年的中國電影,我們不免驚異於它的口號少了,但是口氣大了。
2017年的《戰狼2》用一句「那他媽是以前」與過去的自我決裂;
2018年的《紅海行動》以斬釘截鐵的「勇者無畏強者無敵」完成當下的自我重塑;
而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則憑衝決而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將中國電影指向一條必然的來路和去路:追尋自我的突破。
這一突破之舉,首先在《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和《我和我的祖國》三部電影中有着突出表現。
01
假如將2019年的中國電影事件看作一部大電影,那麼年初上映的《流浪地球》無疑遵循了好萊塢經典敘事結構:開場就是一個高潮。
這個高潮沒有在定格到一個亮眼的票房數字後迅速回落,而是以突破性的科幻電影類型嘗試(事後證明也是奠基),一再延宕我們的高峰體驗,衝擊我們的國產電影認知範疇。
它以令人瞠目的恢宏氣概,把我們代入到一個全球敘事的視點之中——
由於太陽老化,急速膨脹,不久將吞噬地球,人類決定帶着地球逃逸到比鄰星系,為地球尋找新的家園。
該目標共分五步,共需2500年,約一百代人接力完成。史稱「流浪地球計劃」。
在這一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的計劃中,人類的渺小感和人定勝天的力量感,矛盾地交織於一體:
當我們作為個人,我們微不足道;當我們面對宇宙,人類和地球渾然如一,生死與共。
《流浪地球》用一支7000餘人的重型團隊,讓觀眾第一次在大銀幕領略了不輸好萊塢製作的中國科幻大片,並且看到它在科幻類型上的積極探索:
領航員空間站的太空歌劇場面,地球表面千里冰封的末日廢土景象,以及地下城現代科技與貧民窟生存狀態混雜的賽博朋克氛圍,無一不讓我們感受到創作者的用心和野心。
流浪的山水詩意和帶着地球流浪的史詩氣魄,輝映着中國人對故土家園的深沉眷戀情懷。
而這種眾志成城、團結一心的中國式情感,在2500年的宏偉征途感召下,進一步激活了「愚公移山」這一古老的中國文化和精神源動力。
正如毛澤東在1945年第七屆全國人大閉幕會上,所作的名為《愚公移山》的講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
講話中接下來這句,甚至在電影中也有着情節式呼應: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所以我們看到,最終正是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聯合全世界各國人民(救援隊是其代表),化解了木星、地球相撞這個滅頂危機。
而在暑期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裡,陳塘關是否能倖免東海之水結冰摧城的滅頂危機,則有賴於哪吒和敖丙這兩位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
在第二次密鑰通知的加持下,《哪吒》以50.03億的收官成績,將一度領先的《流浪地球》逼停於剎車時代,腳踩風火輪,毫無懸念登頂2019年中國電影票房冠軍鐵王座。
這是中國動畫電影迄今為止最為驚艷的出場,之所以這麼說,在於它完成了此前包括《大聖歸來》等高標之作也沒能做到的一點——對於經典IP的現代性轉換。
這種轉換的徹底性,首先表現在對於原版故事「削肉還母,剔骨還父」這一最具反叛精髓的情節的大膽棄用。
影片中的哪吒,乃天生魔丸,而由於對自身破壞力的茫然無知,再有當地百姓的偏見相持,哪吒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對抗,也就成為本片的主要衝突。
為了凸顯這條衝突主線,《哪吒》的第二次轉換是對「父與子」情感關係的顛覆性改寫。
在這裡,李靖不再是那個視天庭的清規戒律為最高指令的嚴酷執法者,而是一個為了在天劫咒三年期限生效前,讓哪吒做回一個心性正常的兒童操碎了心的父親。
在這兩重轉換之後,影片還將原版故事裡僅充當矛盾導火索的敖丙,和哪吒組成了雙雄結構,使之成為哪吒的一體兩面:一為魔丸,一為靈珠。
他們天性相異,但處境相同:都面臨着自我身份的確立和打破他人偏見的難題。
而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到底是誰在製造偏見?
影片其實交代了偏見的來源。
一是命定的身世,二是人心的偏見,即陳塘關一眾百姓。
問題恰恰出在這裡:我們光顧着心疼那個被雞蛋砸得微微晃動的紅肚兜小孩,那誰來心疼那些沒來由就要挨一下子、水缸碎一下子、房子塌一下子的陳塘關百姓呢?
那雙緊握的小手夠招人疼了,所以那些被折騰得要死要活的百姓,是否就喪失了喊疼的權利?
而這個問題,在結尾的抵禦天雷劫大戰中被加以放大:百姓緣着戰後的巨坑,跪拜於哪吒和敖丙。
這是一個令人感到吃驚的舉動。
由此我們看到,哪吒與陳塘關百姓的關係徑直從敵我走向了主奴。陳塘關百姓對哪吒的態度,徑直從畏懼走向了臣服。
換句話說,彼此有說服力的理解,始終是缺失的。
影片呈現出的哪吒形象,的確是為了實現自我不惜代價的,只是這代價還包含了某種對他人的自我的漠視。
在「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句響亮的口號之外,我想還需要加上一個小小的補充:每個人的命都一樣珍貴。
《流浪地球》和《哪吒》裡,沒有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只有一個個迎難而上的「我」。
同樣,在國慶上映《我和我的祖國》裡,也把「我」放在了建國後70年的7個支點上。
支點的一端,是我;支點的另一端,是我的祖國。
連接兩端的,是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的情感和命運共同體本質。
在總導演陳凱歌的指揮下,七個故事起起落落,創作思路和拍攝手法各有風格。
通常來說,這樣的命題作業,極容易拍成拼貼式的故事集錦,丟失掉一部電影整體性的嚴謹。
但我們還是驚喜地看到,它找到了比以往主旋律獻禮片更為精巧的敘事策略和更加奏效的敘事話語。
這在影片中的具體落點,便是象徵着科學技術發展的道具或事件。
最終,國人與科技的較量,科技對國家的推動,如鐘擺一般,來回搖盪在小寫的「我」和大寫的「祖國」之間,準確而有力地扣合着70年的歷史進程。
我們也會注意到,在這場盛大慶典中,第五代導演中堅力量的當仁不讓:
黃建新先以一部《決勝時刻》拉響禮炮,陳凱歌和田壯壯隨後在《我和我的祖國》中奏響進行曲,張藝謀則用一台彰顯大國風範的晚會打出一個巨大輝煌的休止符。
多方協力加載「春節十二響」程序,從而完成了一次頗為壯觀的建國70周年文藝匯報表演。
02
有別於《流浪地球》《哪吒》和《我和我的祖國》的驚天動地,過去的一年,我們大多數人都像《新喜劇之王》裡的如夢(鄂靜文 飾),或者《兩隻老虎》裡的余凱旋(喬杉 飾),掙扎於一個小人物的悲喜。
我們想得到一個小小的突破,取得一點小小的成績,這樣,假如生活欺騙了我們,我們還能積攢一點底氣,繼續勇敢地活下去。
在《新喜劇之王》裡,如夢想要的突破,是從一個死跑龍套的,成為一名女主角。
為此,她飽嘗一名偉大演員崛起前所必須經歷的艱辛:她的身後是暴躁父親怒其不爭,身邊是出軌男友萬箭穿心,眼前是試戲碰壁的白眼和冷笑,閉上眼,等待她的是天地失靈的又一個天明。
導演周星馳以一種令人費解的純粹而又決絕的方式,將如夢丟入虎狼的現實,或者更準確地說,丟進一方無物之陣,迫使其逼視自己的內心,並發問道:
你為什麼想當一名演員?你有什麼能力當一名演員?
我們看不到她過人的天賦,也看不到她過分的熱愛,如夢的整個行動似乎只能回答:我必須做一名演員。
影片的結局是程式化的喜劇處理:如夢如願入選一部知名導演新戲的女主角。而我們也知道,這不過是如夢一場。
這部電影讓我們感覺到了導演周星馳的某種舉棋不定——
他揚起胳膊帶頭喊出「努力,奮鬥」這句沸騰的勵志標語,塑造如夢這個被反覆打擊反覆悍然站立的小人物形象。
似乎在說,奮鬥不一定產生意義,也像是在說,奮鬥本身就是最大的意義。
同樣讓我們感到困惑的,還有《兩隻老虎》裡,妄圖通過挾持地產大亨張成功(葛優 飾)以實現財務自由的廢青余凱旋。
開篇黑色喜感的「要錢還是要命」只是虛晃一槍,劇情很快轉調為張成功教余凱旋「做個人吧」的溫情之旅。
因為這一槍佯裝紮下去的表面文章都不耐煩做,於是我們既看不出余凱旋綁人謀財的狠,也看不出張成功橫遭不測的懼,誰都沒把誰當真,結果在「我替你辦三件事」上認了真。
以致《兩隻老虎》這首童謠的寓言底色失去了「一隻沒有眼睛,一隻沒有尾巴」的殘酷,只剩奇奇怪怪的天真。
影片裡,天真的余凱旋受困於這樣一個現狀:工作沒了,於是沒錢。因為沒錢,所以結不了婚。他被錢的煩惱推着走,他能想到解決煩惱的方法,便是打劫有錢人。
張成功有錢,他更有愧。本片用對應張成功的愛情、友情和親情三個構成主電影主體的故事,暗示一無所有的余凱旋,以及和余凱旋一樣一無所有的年輕人一個道理:錢好掙,情難還。
電影中,懂得了這個道理的余凱旋,選擇了浪子回頭。而我們知道,困厄他的牢籠,依然堅固。
說到這裡,我們可以說,余凱旋和如夢,實質是一類人:
他們都在外力的推搡之下,前仰後合,東倒西歪,盡最大的努力保持雙腳着地。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安穩地從容地站定,去坐下來思考和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賽道,然後練習奔跑。
而在《平原上的夏洛克》這部2019年最受低估的黑色喜劇里,主人公超英(徐朝英 飾)打從一出生,就找到了自己的賽道,並一條道走到底:凡事都要論個理,更要講個情。
而對理和情的考驗,從來都是一個當頭的「錢」字。
人到中年的超英,為圓一個亡妻的念想,賣牛換錢,決意大興土木蓋新房;
來工地給他幫忙的同村發小遭了車撞,司機跑了,人躺在醫院昏迷不醒。
躺一天,超英就要多付一天的錢,新房便要少去一角屋檐。這是情比錢重要。
此時,一個選擇是息事寧人走醫保大部分報銷,一個選擇是派出所立案等抓人賠償。前者的風險是,多少還是要自己掏點。後者的風險是,抓不到人,就全得自己墊。
事實表明,那邊一立案,超英即要面臨破產——無物證,無人證,無監控。
案子雖然易立不易破,但是理比錢重要。
左是同鄉發小之情,右是傷人要擔責的古理,於是超英和同村另一發小結成哼哈二探進城追兇。
從「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基本常識出發,集合「三個臭皮匠」的人生經驗,發揚「扶乩請神」的民間智慧,在實踐中鍛煉聲東擊西的偵察和反偵察能力,從而為我們奉獻了一出節奏明快、笑料百出和類型辨識度極高的鄉土喜劇。
鬧了笑話闖了禍,影片最後,超英和發小並沒能依靠他們土法煉鋼式探案手段,抓到肇始司機。
但看到這裡,案件的偵破與否已經不再重要——
城市化進程與鄉土中國的碰撞,才是本片更大的看點。
在這個過程中,村落文明的餘韻,鄉間古樸情義的存續,人們對於鄉誼人際的維繫與珍重,都讓淪陷於都市現代化的觀眾,收穫一份久違的無限近黃昏的感動。
03
在去年的青春片領域,上半年一部技驚四座的《過春天》,下半年一部街談巷議的《少年的你》,是兩份令我們感到解題思路有所突破的答卷。
青春這道門,打開它的鑰匙有很多把,兩部電影的導演幾乎不約而同地拿了同一把:動。
為此,《過春天》導演白雪精心編織了一個家在深圳-學在香港的雙城故事,透過空間敘事的新穎布局,將中學生佩佩(黃堯 飾)的青春活力充分調動,使之每日奔波於兩地出境入境,在出和入之間,一個「過」所蘊含的動勢,得到了最大化的蓄能與釋放。
在本片中,佩佩如何「過春天」,取決於她彼時腳下的土地。
當她在香港的時候,她是在度過春天:她能去找已另外成家的香港父親吃吃飯,撒撒嬌;在學校她有個閨蜜阿Jo形影不離。她們有個共同的願望,攢夠錢,聖誕節那天赴日本喝酒看雪。
當她在深圳的時候,她盼望着向春天走過去:家裡總是一刻不寧,母親不是打麻將玩牌,就是時不時帶一個陌生叔叔回來。母女倆之間沒有什麼交流,也談不上什麼了解。佩佩用「失語」表達青春的叛逆。
雙城生活對佩佩在家庭、學校、社會乃至身份認同上的割裂,直到她陰差陽錯,成為一名往返運輸蘋果手機的水客,才得到稍稍彌合。此時,「過春天」也落到了它本有的含義:成功過海關。
而這個「過」,也帶有了青春禁忌突破的意味:
她與阿Jo男友語焉不詳又似乎心照不宣的曖昧試探,通過互綁手機一場戲,散發了欲,也止於欲說還休;
另一邊,在大姐大花姐的賞識之下,她擁有了成人世界的准入證和獨當一面的表現機遇。
只是這個春天雖然溫暖,但卻短暫。
佩佩的雙城跑動和青春躁動,陡然被一雙無形然而有力的手一把捏住腳腕,愈來愈緊,直至無法動彈。
她又回到了最初的那個自己,一切的變動悄然恢復為原封不動。屬於她的春天,究竟什麼時候才會到來?
而在《少年的你》中,高三學生陳念(周冬雨 飾)的春天眼看就要來臨,她是一個好學生,即將考上一所好大學,然後迎來一個怎麼着都比現在好的人生。
但是這個看上去美好安穩的未來規劃,在校園霸凌的蠻暴介入後,陳念再也無法安坐於課桌前板凳上,被迫參與這齣驚心動魄的「貓鼠遊戲」,跑起來,躲起來。
總之,動起來。
到處逃跑的陳念在猶如身體一部分的鏡頭追蹤下,無處躲藏,被殘忍地切割成了因絕望而淡漠的眼神、汗涔涔淚盈盈的面頰、窄小瘦弱的肩膀和孤單無助的背影。
她無法慶幸又逃過一劫,因為她不知道這場遊戲到底何時終結。
本片採用了極端的動態十足的攝影機運動方案,每一個鏡頭都像響尾蛇,人物的一舉一動和一聲喘息,都會打草驚蛇,之後被鏡頭飽滿地捕捉。
粗糲的影像質感和細膩的情緒語言,盡皆以特寫的姿態呈現,像蛇貼着地面無聲游掠,將兇險的氣息注入整個空氣。
《少年的你》是導演曾國祥的第二部電影作品,我們從中看到了自處女作《七月與安生》以來,他的一貫思考:對「少年情」百折不撓地追問和鮮血淋漓地暴露。
在本片中,陳念和小北(易烊千璽 飾)的少年情越是解剖得骨肉分明,那個手持利刃的無邊的存在,越是讓銀幕前的觀眾感到震驚與警醒。
在愛情題材方面,年末一部《被光抓走的人》直接將觀眾放到了審判席,讓我們既做了被告又要充當自己的辯護律師,去打一場充滿悖論的官司:
你如何證明自己擁有真愛?
故事說的是,有一天,城市裡一道白光驚空一現,一部分人消失不見。
經調查,消失的人大多為成雙成對,由此得出一個荒唐又讓人慌亂的結論:
沒被白光抓走的人,沒有真愛。
影片開了一個極具科幻感的頭後,便棄之不顧——被光抓走的人無人問津,徒留剩下的人百爪撓心。
中學老師武文學(黃渤 飾)和妻子張燕(譚卓 飾),就成了「白光-真愛定律」的重點考察對象。
中年人的婚姻生活,有時就像武文學和張燕早晨那場半途而廢的性愛,做起來沒有什麼衝動,做的過程中還能交談從容,最後沒做完的原因也不是因為性能力不行——該給上學的女兒做早飯了。
他們不像第二條敘事線的少男少女,如果你不相信我愛你,那我就為你去死;
也不像第三條敘事線的年輕夫婦,已經離婚的出軌丈夫遽然消失,妻子(和小三)弄不清他為誰付出了真心,還是不甘心。
多年的婚姻生活,讓他們成為了一家人的同時,也成了某種程度上的陌生人。到後來,他們常常只有一個家的抽象概念,漸漸忽略了具體的那個人。
武文學即便是老師,也沒有查看這道愛情難題參考答案的特權。他像一個為了考出好成績無所不用其極的學生:
花錢製作妻子光照當日出城假車票、自曝夫妻房事,在兩人共同參加的同學飯局上,竭力向眾人證明他們有「真愛」。
這種證明真愛的徒勞和狼狽,需要一次同校女老師的甜蜜誘惑,一次妻子疑似外遇的情感危機,才能讓武文學醒悟過來,徹底看清白光投下的陰影所遮蔽住的真相:
真愛是兩個人的事,與世界的兵荒馬亂無關。
緊隨其後,年過六旬的導演馮小剛,用一部《只有芸知道》,以一個過來人的立場,繼續探討了《被光抓走的人》闡之未盡的愛情命題:
兩個真心相愛的人,其中一個因故離世,那個留在半路的人怎麼辦?
馮小剛壓根沒有建構這個命題難度的欲望,甚至直接說出了自己的回答:苦啊。
於是我們看到,為了喊出這聲沉重的苦,馮小剛放下了攝影機,拿起了當初文工團美工生涯一刻不離的畫筆,為我們繪製了一副如冷軍筆下的超現實主義油畫作品:
畫的像真的似的,而它們又真的是畫的。
無論是取景地新西蘭童話般的絕美風光,還是隋東風(黃軒 飾)和羅芸(楊采鈺 飾)二人童話故事一樣的完美愛情,都讓我們感到了無限接近攝影藝術的逼真,而這也意味着,那種終歸是畫出來而非照出來的虛假感也被同步放大。
雖然本片改編自馮小剛好友的真實經歷,但這種純真到近乎作偽的愛情詠嘆,顯然無法得到更廣泛觀眾的應和。
上映近一個月,一個多億的票房成績對於一度曾是票房保證代名詞的馮小剛來說,無疑是失敗的。
馮小剛為此也不免自嘲「廉頗老矣」,但我們若是反顧他的創作路徑,似乎可以說,這更像是一次咬合1994年的處女作《永失我愛》的同主題變奏。
只不過《永失我愛》裡「因為我不能陪你一生,所以狠心半路作別」的純情至死,25年後,變成了《只有芸知道》裡「半路就是一生,相愛就是最遠的路程」的中年感傷主義。
此中的歷歷心境和隱秘體驗,或許馮小剛本就不預備得到太多人的理解。
有的人在為是否擁有真愛而苦惱,有的人在為不能守住一生所愛而感懷,也有的人在愛的城門前,久久不得放行,後來只能寄希望於「送我上青雲」,用自愛和這個世界握手言和。
由滕叢叢導演、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雲》,毫無疑問是2019年最為奪目的女性題材電影。
罹患了卵巢癌的女記者盛男(姚晨 飾),既不能指望自私的父親,也不能指望無能的母親,就連一直渴望的愛情,如今也沒有了可能性。
愛情雖然沒有了可能性,但是性,還是有可能的。
性所能煥發的生命力,是對生命朝不保夕的盛男最大的引誘。
只是在這條籌錢看病和性愛追尋之路上,她還不得不帶上那個心若少女隨時保持綻放的母親,以使形成參差的對照。
本片與上半年上映的《柔情史》有異曲同工的地方,都以跋扈的高唱反調的姿態,通過一對母女的內部對抗和各自為戰的外部反抗,告訴我們在堅硬的男權社會裡,女性的柔情是如何消亡的。
《送我上青雲》更進一步,用一片更尖銳也更柔韌的刀鋒,毫不留情地切進當代女性裸露的傷口,精準地深入、旋轉,挖掘她們的豐富和她們豐富的痛苦,同時剜去那顆會使她們丟掉性命和自我的腫瘤,讓她們健全地存活於世,雖然這健全里有揮之不去的蒼涼。
04
回望去年的國產喜劇片,我們不禁發現它們用了喜劇里慣用的反差手法,跟我們開了一個玩笑:
當其他類型的電影都在力爭向上突破的時候,喜劇片則一再試探我們的下限。
65歲的成龍依然生龍活虎,準時在每年的春節檔給全國觀眾拜大年,用一年一部「龍出沒」(2019年是《龍出沒之神探蒲松齡》)和隔壁的《熊出沒》聯手,全心全意為人民的鬧心服務。
而新晉「喜劇之王」岳雲鵬憑藉越拍越爛、越爛越拍的頑強毅力闖出一片天地,並完全摸准了觀眾的脾氣:萬一您就好這口呢?
於是《鼠膽英雄》這樣一部在沒有科學佩戴手工耿的笑容輔助器前提下極易看出心理疾病的電影,就成了一種惡趣味的公然示範:
儘管我難看如鼠,但你還不是追着我不放嗎?
從開心麻花走出來的艾倫,這兩年更是和岳雲鵬打起了「喜劇爛片一哥」爭奪戰。
《夏洛特煩惱》和《羞羞的鐵拳》讓我們記住了他的呆傻和大力出笑話,而他卻幾乎忘記了怎麼擰麻花,越來越擅長怎麼讓觀眾擰巴。
去年的《李茶的姑媽》沒皮沒臉沒禮物,兩手空空就敢揚言我們是來「笑敬觀眾」的;
今年的《人間·喜劇》加量不加價,防不勝防咣咣兩管JY噴在「人間」和「喜劇」上,逼着歡天喜地去看一場喜劇的無辜觀眾,直嘆人間不值得。
喜劇是冒犯的藝術,但我們的大部分國產喜劇創作者顯然對此有誤解:
在他們那裡,喜劇是成為罪犯還不受制裁的法外之地。
他們強姦觀眾的視覺,勒索觀眾的笑聲,搶劫觀眾的時間,拷打觀眾的價值觀。
試問,這哪一件哪一樁,不得判個五年起,上到無期?
當然,在烏煙瘴氣和體液橫飛的亂象之下,也有值得一說的喜劇作品。
比如年底由《驢得水》團隊推出的《半個喜劇》,便多少讓我們得到一絲喘息,恢復一些笑意。
本片一上來的氣質也和《驢得水》相仿,比如極具戲劇性強度和密度的「時間統一,空間統一,人物集中」的炫技式開場設計,人物性格鮮明到近於癲狂,台詞機敏不失節奏鏗鏘,僅用五分鐘便完全抓住了觀眾的注意力,吊起了我們高昂的觀賞興致。
接下來我們也不難看到,它在精準擊打當下年輕人的愛與怕上,做足了調查功課。
大火烹調了一鍋濃稠的喜劇效果後,開始往裡一把一把添加猛料,愛情還是麵包,兄弟還是女人,聽媽媽的話還是聽從自己的內心,做自我還是他人眼中的我,在在都是兩難。
於是片名暗示的潛台詞呼之欲出:半個喜劇,當然就有參半的憂慮。
《半個喜劇》想要帶領我們在雞飛狗跳之後,去做一個嚴肅的批判性思考,甚至大膽的想象:
一個毫不妥協的人,在這個社會有沒有幸福和自由的可能?
作為一部喜劇,本片給出的答案,看起來圓滿,也空幻。
北漂男孩和北京本地女孩的北京愛情故事結局裡,有愛,也有北京房本,但他們不是一個人人可以參考的範本。
從這個角度看,它的先聲奪人最後也就淪為了只聞其聲不見其行動,「半個喜劇」的寓意,在虎頭蛇尾的劇情推進中悄悄回到了價值中立,成為一句正確的廢話:
生活可不就是一半歡喜一半憂嗎?
眼力勁好的喜劇演員,今年沒有繼續趟國產喜劇電影的渾水,他們扭頭一猛子扎進了懸疑犯罪類型片,試圖打破自己的標籤,也是為了趕在消耗掉喜劇人形象儲存的好感前,避免走上重複自己的不歸路。
比如「屌絲男士」大鵬,先是一部《鋌而走險》,後是一部《受益人》。
兩部電影都是新人導演的處女作,也像是為了大鵬量身定做。
於是我們看到兩個新人(姑且將轉型的大鵬也看作新人)在犯罪類型片上常見的問題:偏愛做加法。
地形環境要足夠複雜(兩部電影都發生在山城重慶),人物角色要魚龍混雜,情節就算不複雜講起來也得像雜耍。
當整個氣氛醞釀到可以開出一朵惡之花,然後就在「惡」的不得已而為之和「花」的好自為之中間來回掙扎。
但在這種節奏感的劇烈跳動之下,無論是敘事邏輯的拍子還是人物塑造的拍子,要麼搶拍了,要麼慢拍了,好比吃酒席,根本沒人勸酒,自己為了幾粒花生米幹掉三瓶二鍋頭,結果就是不可救藥的失控。
而大鵬在兩部電影中塑造的小人物,也存在急於撇清以往的喜劇形象而變得過於嚴肅的情況:
苦大仇深,頷首裝狠,摘了近視鏡的小眼神,一精一精,你不知道他是因為看不清,還是看了太鬧心。我們如果單從劇照看,甚至分不清哪個造型對應哪部電影。
這種同質化的形象塑造,也折射了大鵬對於小人物的刻板理解。
小人物缺錢,但不代表他也缺水洗臉;小人物缺應對大事的經驗,不代表他總得一副天要塌下來的畏縮樣;小人物逼急了也有逆風翻盤的計上心頭,也不代表一件黑色雨衣加身,人物的層次轉折就此完成。
而同樣尋求轉型的「筷子兄弟」肖央,在2017年的《情聖》中度過了中年男人的七年之癢後,重新回歸愛和家,憑賀歲檔的《誤殺》完成一記漂亮的擊殺,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用「影迷的自我修養」為愛女脫罪的感人父親形象。
這種電影知識與犯罪現實的互文,使得觀眾在沉浸於觀影的同時,也不自覺調動起自己的觀影儲備,代入探案視角跟進劇情的進展,從而達成銀幕內外一次奇妙的互動。
《誤殺》既是2019年最成功的影視翻拍,也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國產犯罪類型片。
新人導演柯汶利一鳴驚人,一出手,就展示了於細節處見真章的成熟氣度和抽絲剝繭的類型片拆解能力。
監製陳思誠顯然功不可沒,我們多少可以看出《唐人街探案》系列的懸疑推理質感在本片中的延續:
幾乎與《唐探1》如出一轍的泰國華人聚集區布景,踩着點反轉發轉再反轉的爽文式敘事節奏把握,都有着該系列基因的注入。
這也就難怪陳思誠會將《唐探》網劇這個廠牌亮眼的IP,放心交到柯汶利手裡。
我們樂於見到這種經過市場檢驗的電影人,既能手把手又能大膽放手的培植新人生力軍的模式,得到規模化的鋪陳。
陳思誠和寧浩(專注孵化新導演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這一類導演,還是太少了。
05
在現實關注方面,一月份上映的《四個春天》,是一次溫暖如春的觀影體驗。
北漂導演陸慶屹花去四年時間,記錄自己一雙父母日常相處的點滴,匯入封存的家庭錄像片段,用一種樂天的心態,苦吟出一首格律工整意境悠然的田園詩,帶給我們涓涓的感動。
鏡頭裡,他們忙活年夜飯,互相攙扶着採藥進山,為離家的兒子送行,為離世的女兒傷心。
庭院深深,天台的蔬果架長勢喜人,早春的燕子叫醒了父親的浪漫天真,遲歸的遊子慢了母親手上縫衣的針。
《四個春天》裡的陸家人,說着我們聽不懂的貴州獨山方言,卻表現了每個人都心領神會且心嚮往之的生活狀態,描繪了「唯有田舍老,不聞塵世言」的生活理想,像一間開在人煙稀少處的茶肆,為銀幕前的觀眾奉上一碗溫熱的茶湯,替他們驅除疲憊,卸下行裝。
這種樸素的生活理想,有時不在前方,而在回不去的過往。
在五月上映的《過昭關》裡,就通過一對爺孫情的徐徐展現,讓我們仿佛也不經意間撿起了童年往事的底片,在光陰的淘洗中,一幕幕開始清晰地浮現。
電影開頭,便一瞬間接通了觀眾的童年記憶:
因爸爸忙於做生意、媽媽在醫院待產而無人照管的寧寧(李雲虎 飾),被送到了鄉下爺爺家過暑假。
寧寧本以為是從一種孤單無聊被擺渡到另一種孤單無聊,卻在爺爺發起的「三天抵達三門峽」三輪電動車公路旅行中,不但發現爺爺是一個稱職的玩伴,也從爺爺飽經滄桑的巧手中,得到了商場裡買不到的玩具:
三兩樣廢品可以做成逮魚的工具,隨手拿來的紙張和吸管,轉眼就成了呼啦啦的風車。
而沿途的一樁樁人間見聞:爺爺與荒野養蜂人把酒話當年,長驅千里只為看一眼病危故友的知交零落情,路遇不平要能幫一把是一把的存善心行善行,都讓寧寧學了一堂學校教不了的必修課,在他內心植入一個簡單的真理:
人生就像過昭關,關關難過關關過。
而這種「從前慢」,在影片結尾催人淚下的爺孫互相告別中,也一去不復返。
悠長的假期總會結束,爺爺的「愛的教育」終是短暫。
回到城裡,等待寧寧這樣的中國小孩的,是漫長的《銀河補習班》。等待寧寧父親這樣的中國家長的,是稍縱即逝的《學區房72小時》。
某種程度來說,《銀河補習班》裡的天才工程師父親馬皓文(鄧超 飾)對兒子馬飛的感悟式學習教育,像是《過昭關》中爺爺與寧寧相處方式的現代化升級。
本片中,馬皓文堅信「世界上沒有學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他要用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和閻主任為代表的傳統應試教育進行一場短跑比賽。
和校方談判環節,馬皓文由於實在自信滿懷,對方要價五十,他說這是看不起我,我出一百。
最後談妥的條件是,本學期期末考試中,馬飛若能從倒數考到年級第一,就繼續留校求學;哪怕考個年級第二,馬飛也得退學走人。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馬皓文用對待一個演員的標準,對馬飛實施集訓拉練:真聽真看真感受。
當馬飛從眼前的青青草地中領會「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句古詩的意義,親見馬皓文用科學常識贏得別人的尊重,在翹課看展的旅行中領略祖國的山川河流也差點命喪洪流,馬爸爸的教育,最終通過一場毫無懸念的沖向勝利的期末考試,宣告大功告成。
看完電影的觀眾,就像為孩子報名高價補習班後大呼上當的家長:退錢!
導演鄧超和俞白眉雖然少了之前《分手大師》和《惡棍天使》的拿油滑當有趣,在《銀河補習班》中拿出了試圖認真探討的誠懇態度,但我們不得不指出一個本質問題:油滑慣了的人,真誠起來,也不可避免的處處打滑。
影片一方面想要通過一場突擊補習,來論證只要打開了孩子的眼界、激發他對學習的熱愛,就能作用於考試成績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展現出的成果更像是一切盡在掌握的軍事演習——
馬飛顯然不僅是打開了眼界,也被打開了看到參考答案的天眼。否則如何解釋一個幾乎全程都在玩的差生,說考第一就考第一,還是全年級?
影片沒有正視應試教育和素質教育的真正衝突,也迴避了教育改革這個根本性的制度性問題,但卻想要災難和科幻的多類型融合,想要天下所有的父親都能得到感動和啟發,想要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學會學習並熱愛學習,而這種什麼都想要但又不願有所付出的心態,正是油滑的典型表現。
和馬皓文同樣貴為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副教授傅重,沒空關心銀河的事兒,他眼下面臨的難題就像他的名字:《學區房72小時》內要解決的緊急任務,迫使他負重前行。唯有如此,他的寶貝女兒才能進入市重點小學。
《學區房72小時》是2019年幾乎被忽略的現實主義佳作。
這台戲沒有熟臉演員,也沒有獵奇的事件,甚至也沒有一個不那麼像普法欄目劇的片名。
學區房三個字,有着國人一望即知的潛台詞:學區房不得不買,學區房十分難買。
圍繞它展開的72小時,除了直到簽訂交易合同前持續每一分每一秒的焦慮,還能是什麼呢?
如此一來,本片從「購買學區房」這個不起眼的小切口,挑開中國家庭結構性大動脈的高難度動作,便在無人欣賞中悄然完成。
麻木掩蓋下的驚心動魄,只能被迫繼續麻木。
06
過去的一年,我們看到曾經以「大」為綱的主旋律電影,開始注重以「人」為尺度,將電影敘事從符號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緊張捆綁中鬆開手腳,在了解和運用電影這門藝術形式上投入更多的思考,從而達到弘揚主旋律並吸引觀眾自發參與、自覺認同的目的。
《烈火英雄》《中國機長》《攀登者》和開篇提及的《我和我的祖國》,便是這一主旋律敘事變奏的最新成果,並取得了顯著成效。
它們在題材選取上,更關注當下性和呼應時代脈動。
例如以「大連7.16油爆火災」為原型的《烈火英雄》和以「四川航空8633號班機事故」為基礎改編的《中國機長》。
它們在敘事策略上,更關注場面營造的敘事功能,而非場面的大鳴大放。
《中國機長》裡故障班機穿越雷雨雲的驚險調度、《攀登者》中命懸峰頂的天人交戰,帶給觀眾的不僅僅是視聽震撼,還有敘事的整體推進;
它們在創作手法上,更關注災難、動作類型片的多元融合和先進電影技術的搭配組合,逐漸確立了「主旋律」的商業類型片氣質。
用生動的故事代替生硬的說教,正在成為大銀幕上的現實。
但與此同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一盛行於wg期間的「三突出」文藝指導理論,仍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烈火英雄」江立偉(黃曉明 飾)的毀容臉(突出英雄人物的犧牲感)和「中國機長」劉長健(張涵予 飾)仿佛從杜莎夫人蠟像館走出來的僵硬造型(突出英雄人物的偉岸),便是對「三突出」的再突出。
主旋律的敘事變奏,仍需一變再變。
過去的一年,我們也看到以「小」為美的作者電影,開始走向市場,用個人話語向大眾表達、與大眾對話的嘗試,少了以往交流的無奈,多了一些互相理解的可能。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裡那堆映照的姜紫成(秦昊 飾)忽明忽暗的火;《撞死了一隻羊》裡名字都叫金巴但各懷心事的兩個藏族漢子;《陽台上》這場幾乎走向極致的視聽語言實驗……
都成為我們2019年不可多得的閃閃發光的觀影時刻。
電影是一場主題未知但如此誘人的聚會。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方車站的聚會》是2019年中國電影最得當的句號:
大家相逢一笑,互開一槍,報站的汽笛鳴響,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2020年,希望中國電影在對的方向上,威猛地走下去。
- END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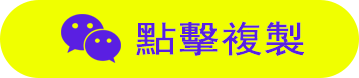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我聽別人說過,值得推薦的情感機構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