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內容為虛構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楔子

他總覺得那個時候的柳枝,溫柔的像情人的手,那個時候的雪,靜美的讓人想要落淚,他走在鄉間的路上,跟身旁的耕牛說着一件件太宗皇帝,中宗皇帝還有玄宗皇帝時候的故事,牛生了小牛,老了,死了。終於有一天,他也老得快死了,他跟老牛的孫子說,我來給你講一件開元年間的舊事吧,你的爺爺都沒聽過的故事。
一騎雪積饒,暗香紅袖招。
開元二年的春天,開始於一場漫天的大雪,陸陸續續從清晨飄至傍晚,無半分要停的模樣。
從弘文館出來的時候,孔懷遠牽着他那匹伴隨了三個多月的灰驢。眼下已是足足下了一天的雪,積下半尺來深,落腳上去,便是「咯吱咯吱」的聲音,弘文館位於宮城之西,轉過順義門,安靜的有些可怕,倒顯得腳下不緊不慢的聲響格外清晰。
孔懷遠抬頭看了看灰濛濛的天,耳邊傳來不遠處炮竹聲,孔懷遠這才回過神來,原來時值上元佳節,方才明了為何適才四周靜寂無聲,原來布政街此時恐怕所剩人已不多,都趕去東西二市觀賞焰火去了。
自太宗皇帝親率六騎至渭水與劼利可汗隔河而對,劼利可汗攝於太宗皇帝聲威,與太宗皇帝議和,便橋會盟之後數年間,或和親或行兵事,不幾年天下共稱太宗皇帝為「天可汗」,是以,邊疆安寧,四海平定。武氏改朝以來,嚴刑苛法,政治清明,內臣皆安,大唐行至開元以來,漸漸露出了盛世的景象來,長安乃唐朝國都自不必形容其繁榮勝景。
孔懷遠正沿着布政街雪道上若有若無一道蓮花足跡緩緩行走,其時女子都喜着南北朝流傳下來一種布鞋,名為「步步生蓮鞋」,意即行於道上,會在泥土上印上蓮花圖案,此時雪積已深,夜色迷茫,若不是孔懷遠自幼眼神靈便,怕還真看不出來,雪下竟是藏着蓮花。
他正暗自嘲笑於不知誰家女子如此瑞雪,竟着布鞋出行,當真是片刻之後便要狼狽不堪了。恰值此時,聽聞身後傳來呼喊聲,「懷遠兄,懷遠兄!」懷遠是他的字。
孔懷遠回頭一看,原來是中書舍人蕭嵩之子蕭瑾瑜,孔懷遠慌忙回過頭來,「原來是瑾瑜兄?不知。。。喚我何事?」
孔懷遠祖上本是貞觀凌煙閣十八學士中的孔穎達,太宗皇帝即位後,命其為國子博士,編訂《五經正義》,唐初大儒,以孔氏最為顯貴,太宗皇帝稱讚其為「關西孔子」,實是了不得。
然則子孫不肖,再加上武氏亂朝,孔家後人秉承儒子之本分,針鋒相對不肯附隨,所以幾代下來,祖上的榮光十停中就沒剩下半停,及至孔懷遠父親孔少華一代,只兄長孔少忠之子孔競任職親勛翊衛羽林郎將,倒是個正五品上階的職位。
孔懷遠父親淡泊名利,在老家冀州衡水耕田。長兄孔少忠卻自幼熱衷功名,但只恨無房杜之才,庸碌半生,臨到老來,這份心思不見平定,倒是越發的繁盛滋長,他膝下一子一女,千方百計將長女嫁於宰相姚崇一家遠房親戚,才換得幼子孔競得進金吾衛,那原本也是孔競本身不愛學問偏好武鬥,一身本事十分了得。
孔少華只有一子,出生時,孔少忠給取的名字孔潔,字懷遠,自是與孔競字念達一個意思,希冀二人能念着祖上孔穎達的榮光,孔穎達字沖遠又字沖達,其中含義自是巷尾童子也不難明了。
不幾年,孔少忠使盡本事想盡辦法相托,卻都不能給孔潔謀條好路子,不知怎麼地,事情傳到姚崇耳朵里,姚相便將他送入弘文館,自是看在其祖孔穎達之盛名。孔懷遠進弘文館三月以來,只見館內皆是紈絝子弟,家資殷厚,獨獨自己身無長物,一直妄自菲薄,所以幾乎沒和任何人打過交道。這時見蕭瑾瑜喚他,原本並不相熟,一時吶吶不得語。
蕭瑾瑜卻是淡然一笑,「懷遠兄幾月獨坐,瑾瑜深慕,今日見兄獨行,一時心動,願與兄並肩談論。」
孔懷遠聽到「幾月獨坐」之說,心裡不由暗裡苦笑一聲,他學武不成,文事無功,心中常自嘲廢人,哪裡有半分氣概,這時見蕭瑾瑜氣質敦厚,溫潤如玉,那份自低之心越發的強烈。當下忙拱手前請,「瑾瑜兄先請!」
蕭瑾瑜將馬韁挽了一挽,與孔懷遠並肩行走,一時間兩人似也找不到話說,只聽見遠處煙花頻閃,腳下「咯吱」之聲不絕。
孔懷遠見蕭瑾瑜身旁馬匹十分高大,他們文人多學江湖遊俠兒,身配長劍,分量倒是很輕,馬匹四肢細長,多半也是為了好看,再看自己瘦驢在側,一身青衫平時不覺狼狽,這時倒顯得很是寒酸。
又是暗暗嘆了口氣,不由生了分離之意,便抬手對蕭瑾瑜說道,「瑾瑜兄,天時已晚,小弟這便歸家去了,再過片時,恐怕閉門鼓響,宵禁起,撞着金吾衛夜巡可就不好了。」
蕭瑾瑜哈哈一笑,「懷遠兄當真是治學刻苦,難道竟不知上元佳節,三日金吾不禁麼?也罷也罷,咱們且去崇文街走走,懷遠兄京城獨居,晚歸也無不妥,只管隨我去吧!」
孔懷遠不由暗罵了一聲自己竟不知金吾不禁,這時再找別的藉口也不合適,只是對蕭瑾瑜的念頭越來越摸不透了,自己獨居長安,無才無識無財無勢,不知他到底打的什麼主意,聽聞長安士子頗好龍陽,莫非……孔懷遠驚恐的看了蕭瑾瑜一眼,雖是心中覺得不妥,但他性子自幼懦弱,不願拒絕別人,只是緩緩隨着蕭瑾瑜朝前走。
不多時,二人轉入西市,蕭瑾瑜卻突然停下來,對孔懷遠道,「懷遠兄,隔壁便是柳依教坊司,崇文街會軒樓的沁芳釀雖是不錯,但柳依坊的醇酒也不差,況且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新舞,不如我們且往蘇白巷去,前方不遠便是!「
孔懷遠「啊」了一聲,連忙擺手,他雖赴京不久,也知所謂教坊司到底是個什麼地方,官家教坊司所謂藝妓,這種勾欄暗巷之處只怕肯定就是暗娼窩了,他自幼教誨雖不是甚嚴,但也知煙花之所,君子避之。
蕭瑾瑜又是一笑,「懷遠兄不必擔心,此處雖是小巷,但柳依坊里卻不儘是齷齪之人,柳依取的就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意,想來坊間主人也不是俗人,懷遠兄只管放心,絕不至侮辱斯文。」
開元年間風氣甚是開放,「教坊司」是官辦妓院,其中的妓女主要是歌舞妓,通常要大價錢才會陪宿,高級妓女多出身比較高貴,因為父輩得罪權貴才淪落為藝妓,也即歌舞伎之類。
文人騷客流連於勾欄妓院倒也傳出了不少美事,是以蕭瑾瑜並未覺得有何不妥。孔懷遠本不願去,但這時見他相邀,只得苦着一張臉不語,但他年紀尚輕無甚見識,心中也頗有些躍躍欲試,常聽聞風塵之中也有才女,一時有些期待。
說話之間兩人便到了那柳依坊門前,只見門前對面有個小小茶攤,斜倚着一個和尚,兩人都有些驚奇,只見和尚念經,倒不見和尚做生意。蕭瑾瑜眼裡多了些鄙視,孔懷遠不明所以,蕭瑾瑜言道,「這個僧人倒也是有些來歷的,你卻猜猜看,他如何稱呼?」
孔懷遠陪笑道,「小弟不知!」蕭瑾瑜將馬韁遞到迎來的教坊司門人手上,「哼」了一聲,「太宗皇帝之時,會昌寺出了個淫僧辨機,與太宗皇帝十七女高陽公主私通,雖說最後腰斬受懲,但不知民間竟傳成佳話,是以有些僧人不知檢點,特立獨行播散妖名,對面那個僧人乃佛門弟子卻取個道家名字,自稱清虛和尚,真是不知檢點!」他口中連續兩次不知檢點,想是對這些無良僧人十分鄙視。
唐朝本尊崇道家,高祖便是信道煉丹的,到了太宗卻是推崇佛法。其時會昌寺常常有皇親國戚前去拜佛,辨機就是會昌寺的一位高僧,高陽公主與辨機之事,孔懷遠倒也聽聞過,由於高陽公主嫁於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卻與沙門僧人私通,所以皇室大臣之中,自是言之必罵。
想來因為房玄齡乃朝中權臣,太宗皇帝雖是饒過高陽公主,但也將其禁錮,終生不見,所以官面史書都極盡毀譽之能事,將這段秘聞寫的腌臢不堪,其中隱情事隔幾代已不大清楚,但孔懷遠卻常常同情那兩人,總覺得辨機和尚若不是因為這段孽緣,必定是一代高僧,高陽公主若不是恰遇辨機和尚,也不會仇恨一輩子痛苦一輩子。
倒是後世出了不少沽名釣譽的僧人,給這段情史蒙蔽了灰塵,想起來,孔懷遠也嘆了口氣,這時兩人坐騎都已交付,正踩着剛掃過的直道走入門去,他突然心中一動回頭看去,只見那清虛正朝着自己微笑,笑容里恍惚帶點什麼東西,指了指天,並沒有講話。
孔懷遠恍恍惚惚轉過頭隨着蕭瑾瑜進了暖廳,只見一名妖媚女子正在暖廳中央閣台上曼舞,蕭瑾瑜連忙拉着孔懷遠,「懷遠兄快看,這邊是柳依坊坊首熙雯姑娘,傳言中大家都稱她為熙雯仙子,跳得一支好舞,名為昭雪破冰舞,嘖、嘖。。」孔懷遠差點便「撲哧」一聲笑了出來。
方才見蕭瑾瑜一副謙謙君子模樣,這時簡直就是登徒浪子,嘴裡竟是連「嘖嘖」聲都出來了,也不管他,孔懷遠抬頭看去,也是目瞪口呆,只見那女子一襲白裙,臨空飛旋,各種指法腿法變換迅即,這還罷了,難得是腰肢僅盈盈一握,一道白色布條纏於腰間拉至房梁,僅靠腰力,那女子將一身白衣舞得似白雲繞身,飛雪飄散,孔懷遠這才明了為何蕭瑾瑜沉迷若此。
他細細一看,那女子白沙遮面,但細細一眼便能看到長相,朦朧之間依稀可見細眉圓臉,薄唇淡紅,臉色白皙。孔懷遠只聽耳邊蕭瑾瑜還在唏噓道,「怎可嫵媚如斯?」
孔懷遠痴了一會兒,扭頭看去,只見眾人都一副樂不思蜀的模樣,只有角落裡一張小案旁,坐着一名女子手裡捧杯低斟淺飲,不由疑惑起來,這女子不像是藝妓,也不若訪客,倒真是奇怪的很。
那女子似乎知道孔懷遠正在看她,抬起頭來瞥了一眼,孔懷遠只覺一道冰雪從頭淋到腳,心裡似火燒卻又好像有團冰怎麼也烤不化,一時間面紅耳赤,女子勾了勾手指,孔懷遠像是魂也被牽去,直挺挺走過去,只聞到一陣不知緣由的香氣,女子道,「坐下!」他便老老實實坐下。
兩行彩箋語,風雨隨君去。
第二天清晨起來的時候,孔懷遠還是懵懵懂懂,關於昨夜見到那女子之後的事情,竟是模模糊糊一點也記不清楚,只記得那女子的名字喚作玉彤,一身紅衣,長相竟然都記不清楚了。
午間課罷,蕭瑾瑜與學子們暢聊興起,並沒有再和孔懷遠打過招呼,孔懷遠雖是家境窘迫,人也沒有什麼長處,心中常常自低,但自尊心卻又十分強烈,他見蕭瑾瑜並不同他交往,也懶得再去和他多言。
只見那幾人拉着蕭瑾瑜不知講到些什麼,蕭瑾瑜十分為難的模樣,但終究點了點頭。不多時,傳來消息,原來博士午後休憩感染風寒,下午竟是無課了。
蕭瑾瑜幾人連忙呼擁而去,孔懷遠單單一人留在弘文館內,嘆了口氣,又朝昨日蘇白巷行去,行至門前,發現柳依坊的大門竟然緊閉,這才想起,坊間由於金吾不禁,昨夜狂樂一宿,今日估計都休息着。回過頭看茶攤,那個僧人竟也不在,孔懷遠左右踟躕,想了想,騎上驢子,便朝金光門行去。
一路只見西市到處皆是行人商客,其間也有不少碧眼紅毛番邦之人,開元時唐朝國力強大,四方皆伏,所以見到外邦人倒也不算是什麼奇事,只是他也並沒有留意於街道上行人,心中一直不是很安寧,自昨夜見了玉彤姑娘之後,總覺得恍恍惚惚。
今日莫名其妙跑到柳依坊已經是難得的大膽之舉,結果竟是沒見着,不過他暗暗思量,即便是裡面仍在迎賓,他估計也不敢進去,畢竟自己家境貧寒一無所長,去了也只徒增笑耳。
正思量間,已經出了金光門,來到一所大寺前,上面金光閃閃三個大字「天祚寺」,他昨日看見那僧人指了指天便知道,僧人來自這個寺廟,長安城內,含「天」字的僧寺便只此一座。知客僧帶他進去之後,他便問是否有一名清虛和尚。那知客僧本來彬彬有禮,聞聽所問之事,臉色馬上冷了下來,遙遙指了指西北向的一個小屋,便頭也不回的去了。
孔懷遠嘆了口氣,看來這清虛和尚跟自己一樣,也是個不招人待見的人。行至門前,敲了敲門,裡面傳來一個清越的聲音,「孔施主請!」
孔懷遠踏進門來,只見裡面一張舊塌,一張破案,坐着一個眉目疏朗的和尚,豁然便是昨天那個賣茶人,孔懷遠正要行禮,卻見屋內四牆上竟然畫滿春宮圖,圖畫中女子摸樣不甚清晰,但一眼咋看竟是昨日的玉彤姑娘,他心中雖不曾仔細想過,但實已將那女子視作仙子,這時如何不怒。
當下閉目不觀,大怒道,「淫僧,昨天我見你眉目之間倒有些聖人之氣,沒曾想你果真是淫穢不堪,侮辱佛門!還不速速收去,否則。。。且等官家來收拾你!」
清虛和尚淡淡一笑,「施主,我終日坐休於此,視之坦然,為何你坦蕩君子,反倒是閉目不關,說來到底是你心中不寧,還是貧僧淫穢不堪?」
自南北朝時期原來,西方僧人前來傳道,往往便與中華儒者、士人進行辨道,長此以往,沙門弟子竟是都休出了一副好口才,這時清虛短短几句說出來,孔懷遠哪裡能夠回擊,只在口中反覆念叨,「淫僧,淫僧……」想來是已經氣急。清虛和尚卻在那淡淡的笑,「孔施主,我自西方來此,足足三月,便是為了你而來!你難道不想知道我來的原因麼?」
孔懷遠氣鼓鼓,只閉着目,想離開,卻又不甘心,心想萬一日後別人來此,玉彤姑娘的身體髮膚不就全被看去了麼,今日無論如何也要把這些畫叫他收去。
他在這裡左思右想,那廂清虛和尚卻在絮絮叨叨的說,「前年間,經輪阧轉,示轉世靈童生在中土,我師尊盤算一年有餘,五個月前佛光顯於弘文館,我東行一月,才至天祚寺,這裡佛門弟子,全無靈心,只有方丈倒還有些神通,將我收留,我便每日自生自養,擺攤賣茶,為的便是師尊開示,聖童降於此處!施主,你可知,那人是誰?」
孔懷遠雖說腦子有些恍惚,這時也知道清虛所指了,一驚卻把眼睜開了,只見牆壁上哪裡有圖,不過一些菩薩畫像,跟玉彤姑娘更無相似之處,更是連話都講不出來,清虛和尚一指孔懷遠,「施主,便是你了!」
孔懷遠大笑,「和尚,你當世人都是傻子麼?開什麼玩笑!」這時卻是怒極氣極,講話都講得不再斯文。也不管那和尚再說什麼,掉頭便去,清虛也不攔阻,只在後面高聲道,「施主,紅粉骷髏,趕快回去原地吧,你父親將要遠行。記着和尚不是清虛,乃善無畏,下次再見時可要記得!」
孔懷遠哪裡理他,心中暗道絕不會有下次,只是聽着他說父親即將遠行,心中不由咯噔一下,快步離開。善無畏嘆了口氣,「有慧根,卻無緣法!」
孔懷遠回到住處,只見門口停馬樁上繫着一條馬韁,旁邊站着一匹高頭大馬,識得便是昨日蕭瑾瑜只坐騎,旁邊一人左右徘徊,十分焦急,正是蕭瑾瑜,見孔懷遠來到,蕭瑾瑜連忙拉着他,遞出一張彩箋,「這是玉彤姑娘叫我帶給你的,昨日你醉的糊塗,不知何時自己離去,玉彤姑娘便托我轉交於你,今日課間十分繁忙抽不出功夫,課罷之後又被拉去飲酒,回來尋你時竟是到現在才找着。」
孔懷遠打開彩箋,只見上面娟細小字寫着兩句:寂寞空閨遮青絲,風塵場中望君憐。角下三個字「玉彤字」,孔懷遠痴痴站了半天,一時之間心潮澎湃,狂喜的簡直想要呼喊,但卻強壓住馬上將要出口的笑聲,心跳震得整個胸腔都噗通作響。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蕭瑾瑜,就向蘇白巷行去,蕭瑾瑜也瞅了幾個字,大致明白是怎麼回事,但他心情比起孔懷遠要沉穩許多,畢竟只是個旁觀身份,沉吟了片刻,便不聲不響同着孔懷遠去了。
兩人路人速度極快,這自然是因為孔懷遠心情急躁,不管不顧,一再催促蕭瑾瑜的緣故,才到蘇白巷口,竟逢着金吾衛翊衛引駕檢校曹明正在巡街,孔懷遠這才大吃一驚,今日正是上元第三日,明日起便要宵禁了。只是曹明這時前來巡街作何?
那曹明也看見孔懷遠了,他兄長孔念達未曾晉升之前也常與曹明一起巡街,是以曹明跟孔念達十分相熟,也見過孔懷遠幾次,這時連忙過來,「孔公子,你兄長叫你速速去他府上,聽說令尊好像是過世了!」邊說便看了看幾人所站的位置,不由心中思忖,「這孔公子竟然也留戀煙花地!須得讓念達管治管治。」
孔懷遠一聽,心中登時涼了一大半,他父親和藹可親,管教他也不嚴,兩人倒時常像兄弟一般論道談經,這時聽見說父親過世,只覺腦中一片空白,那曹明已經走遠,蕭瑾瑜連忙搖了搖他,「懷遠兄,趕快去你兄長家吧!你先用我的坐騎。」
孔懷遠這才反應過來,爬上蕭瑾瑜的坐騎,只說一句,「明日瑾瑜兄到我兄長家取回。」便快速跑去,到了孔念達家中,只見素色衣裳都已做好,孔少忠性子嚴肅,這時臉上面沉如水,「你且速速歸家,弘文館之事我替你辦,守孝之後咱們再說。」
三生無緣事,泣血楊柳枝。
三月的光景,江南的柳絮都已漫天飛舞,然而北方的柳枝卻還剛剛發芽,此時已經是開元四年的春天,自父親駕鶴西去之後,孔懷遠便在父親墓便結廬而居。
孔少華素來忠厚,鄰居鄉人只見相處和諧,這次他過世,便在山腳尋了一塊風水寶地,南面便是山,北面卻是一條河,孔懷遠每日便讀讀書寫寫字,日子過得也算踏實,對父親的思念漸漸便放下了,起先回到家的時候每每覺得痛徹心扉,後來倒是父親留下的家信反倒寬慰自己看開。
沒多久,伯父的家信送到,不知怎麼地傳言他在京城留戀煙花地,不務正業,還跟一個風塵女子接下孽緣,老母親又是生氣又是傷心,孔懷遠估摸着怕是開元二年那次柳依坊的事情傳了出去,但他雖自認清白,對玉彤姑娘的那份心思卻越發的重了,母親痛罵,自己也不好還嘴,也懶得再與人爭辯。
兩年下來,倒是生了厭世的念頭,整日裡讀一些佛道的經文書籍,偶爾思量起那個夜晚初見之時,玉彤姑娘的樣貌倒是越發的清晰起來,想來也是可笑,那時初見第二日便不記得那人的模樣,如今時隔兩年反倒越來越清晰了。
這一日,風和日麗,三月的春風吹過,河邊楊柳依依,他便捧着嵇康的《養生論》,新手翻閱。
正在愜意時,忽聽到馬匹的響鼻聲,他只覺心往嗓子眼一提,兩年之前接到玉彤彩箋時候的那種感覺再次出現。然而,人卻好像入了魔一樣,站也站不起來,動也不能動,只聽到身後一個女子的聲音,「呆子,我來了!」一陣香氣隨着春風而來,那是前年的元宵曾經嗅到過的,直到現在還這般清晰。
他扭頭一看,一個紅衣女子亭亭而立,眉目如畫,巧笑倩兮。那一刻,孔懷遠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只剩下了自己和那個女子,就那麼輕輕的笑着,「呆子,我來了!」
「你來了!」他好像也只會說着一句話。
三月的春風溫柔吹亂了紅衣女子耳畔的長髮,他伸手卻還是不敢靠近女子。女子還是在那裡淡淡笑着,「呆子,我帶你走吧!」
他沒有講話,只是跟着那匹馬,他想,這輩子若能做他身邊的一匹馬都會比做人幸福吧。他們走過了三月的溫暖春風,看過了四月的雨中雙燕,折下了龍鳳山上五月的桃花,沒有講話,就這樣一直走着。
直到有天,女子問他,「你為什麼不問我怎麼來的?」他才傻乎乎的說,「哦,你怎麼來的!」
「笨死了,我怎麼看上你了呢?」女子還在那笑,「我把妹妹,就是熙雯送給你那個好色的朋友了,然後用了兩年我妹妹才從他口中吊出了你的消息。你那個朋友嘴可真緊。」
孔懷遠心中一酸,當初母親知道這件事時,他就知道母親河伯父肯定不會允許家族中有人跟煙花女子有關聯,所以蕭瑾瑜肯定會在伯父的請求下攔阻自己,只是這兩年玉彤不知道想盡了多少辦法,竟然連妹妹都送了出去。
「我和妹妹本是犯官的後人,妹妹性子柔順所以能接受在那裡賣舞,我卻不願,我用了不到一年就把柳依坊弄到自己手中,我們姐妹二人,都跟自己說,將來一定要找個如意郎君,妹妹雖說因為你嫁給了蕭瑾瑜,但多少也算得償所願,唉,可惜了我,看上了一個傻乎乎的男人。」
女子伏在馬上,絮絮叨叨的說,孔懷遠不知道怎麼地就覺得心中就這樣慢慢的暖了起來,這個女子,初見時就一副冷漠的模樣,那冷冷的一瞥幾年後自己還是覺得心中一涼,現在聽她講身世,說的那般輕巧,想起來也不知道以前吃過多少苦,這樣的女子,必定是一副冷漠堅強的性子,而在自己面前卻總是言笑晏晏,也不知道怎麼就對自己如此青睞。
「像我們這樣的人,在花街暗巷中生活,早就不知道見過多少男人的眼睛,我看見你時,覺得真是可笑,怎麼一個男人好像竟然畏懼世間所有的人。對於別的女人來說,你這樣的男人恐怕不會招人喜歡嗎,然而看到你,我卻那般沒出息的心動了,你還怕我嗎?」
「怕!」孔懷遠脫口而出,是的,他怕她,從第一眼開始就怕,但就像雪,自己冰冷所以熱愛溫暖,明知靠近了便會融化,卻還是不能抗拒自己靠近的欲望。他想起了清虛和尚房間裡的畫,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時候竟然突然想起來那個,他想,只有那個時候他才不怕這個女子,才會心中陡然生出保護她的願望。
女子沒有再說,孔懷遠原本還想問當初那張彩箋,最終還是什麼也沒說,他心中一直在害怕,不僅僅是怕這個女子,還有自己身後的衡水的那個家,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然而心中卻總覺得隱隱有什麼不妥。
玉彤抬頭看了看天,說,「陪我一起到山頂看看吧,我們還從來沒上去過呢!」
龍鳳山的桃花比山腳開的晚,他們上到山頂的時候,夕陽西去,山間漸漸冷了起來,孔懷遠解下袍子披在玉彤的身上,女子卻直直的看着他,「抱着我!才會不冷!」孔懷遠傻傻的等了一會兒,伸出手來將女子擁入懷中,那麼柔軟的身體,他的心已經狂亂的沒有邊際。
山頂風漸漸起來了,他聽見懷裡的人說,「我知道,我們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在一起的,就算我放棄我用盡心力得來的東西都不行,因為你不敢。我去你伯父家的時候,你伯父罵我說我是個娼婦,說今生今世我們都不可能在一起,除非天地倒懸,海枯石爛。」
女子說着說着,眼淚流了下來,這是孔懷遠第一次看見女孩子哭,他以前總覺得形容一個人心都碎了很荒謬,此時卻覺得這句話簡直太淺顯了。
「抱緊我!你能不能答應我,不管將來你和誰在一起,一定帶着我走到你伯父前告訴他你會娶我!你一定會娶我,好不好?」
孔懷遠擦了擦面上的淚,「怎麼會呢?我會娶你的!」山間的風越來越大了,女子將面龐拭乾,拉着孔懷遠就向山下走,「我們不要再哭了!天冷了,我們下去吧!」
只有孔懷遠邊走邊想,她性子強硬才會因為喜歡我而忍住氣,可見伯父那句話委實已經將她傷透了,但這卻是只有自己才能幫她挽回這口氣和顏面,一時間心如刀割,假如你深愛的人被人深深傷害而卻無能為力,該是怎樣心痛的感覺?
山下就是龍鳳鎮,女子再沒有說一句話,只是進自己房間的時候,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說,「你過來!」孔懷遠走進房間,心跳得厲害,他好像盼望着什麼但卻不敢想,又想迴避,女子解下了自己的頭飾,坐在窗台前,背對着他,「來!」
孔懷遠慢慢靠過去,女子解開自己的領口,抓住他的手放進去,「解開我的衣服!」孔懷遠只覺得一陣溫軟,心跳的愈發強烈,所有的血都衝到腦門上去,連呼吸都似乎已經停止,他猛的扯出手來,「不,我會娶你的!」連忙走出房門。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講出那句話。
頭頂上月朗星稀,他深深的出一口氣,按住強烈的心跳,站在門外靠住牆壁,害怕自己會站不住,口中只剩一下一句「怎會這樣怎會這樣?」
這一夜,他幾乎再也沒有睡着,聽着一夜蛙聲,心猿意馬,清晨時在玉彤門前徘徊了兩個時辰,都不敢敲門,直到日上三竿,他心中不安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拉開房門一看,只見被褥整齊,暗香猶在,只窗台邊留下銀色頭飾一枚,他認得那是誰的,終究還是走了麼?
四季花常開,心死人何在?
開元四年年末,金光門天祚寺外一個青年公子牽着一匹黑馬站立許久,嘆了口氣,「光陰無情,多年前我到這裡來還是一頭矮驢陪着我,如今時過境遷,卻不知道故人是否還在?」
知客僧引着他走入裡面去,「施主可是要拜佛進香?」孔懷遠低聲道,「請問以前這裡有位清虛和尚,現在還在麼?」知客僧一怔,「施主問的可是善無畏大師?」孔懷遠依稀記得清虛和尚曾經說過自己真名,點了點頭。知客僧哭喪着臉說,「現時大士卻是在會昌寺,敝寺廟小,留不住菩薩。」
孔懷遠笑了笑,「雖是不在,我既然來了,那就拜拜佛吧!」只是心中暗暗道,佛真的能懂世情麼?半年前玉彤離開後,他因為擔憂母親,回到衡水,母親卻是無論如何也不准他出門,直到年末伯父說,弘文館假期已到,須得回來上課,母親這才放行,這時他跪拜佛祖,心裡卻全是塵世執念。
及至會昌寺,見到善無畏時候,孔懷遠發現他竟然還是只住在一個小閣內,只是牆上再無春宮圖,倒是一臉莊重正在打坐。
他在如房間,善無畏微笑合十,「和尚不念經,坐堂聽春吟。」孔懷遠不由一笑,「和尚,我至今見你兩面,你竟不能正常一次麼?第一次見你,房內放滿春宮圖,這次見你,冬梅已怒放,和尚卻叫春!」這時善無畏已是天下聞名,玄宗皇帝視其為西來聖僧,長安城內傳播佛法,然而孔懷遠卻還只是覺得他是個俗世的花和尚,隨口開起玩笑來。
善無畏依然不慍不怒,「如來不動,聖人以萬物為心!和尚也有慾念,奈何奈何?」
孔懷遠奇道,「不是說和尚斷絕七情六慾麼,怎麼還會有欲望?」善無畏搖了搖頭,「你還是差了一點佛心,昔者濕婆大神於恆河之畔交媾,百年不止,天神尚且有欲望,和尚如何不能有?」
孔懷遠笑道,「那和尚與凡人又有甚區別?」善無畏笑道:「佛法修到境界之時,男女之愛只是小道,指觸眉眼相望皆可有男女之愛,佛法的道理就是超越男歡女愛,然後忘卻情愛,得窺天道!」
孔懷遠聽到「眉眼相望皆可有男女之愛」不由心中一動,原來看一眼就是情慾麼?他恍恍惚惚卻沒聽到善無畏後面說的什麼。善無畏看他模樣,嘆了口氣,「還是入了魔障,到底是哪裡缺了佛緣呢?你去吧,施主,日後若有所悟不妨再來尋我。」
觀看本章後續內容,請購買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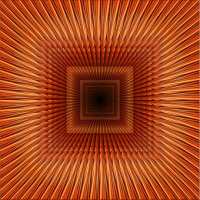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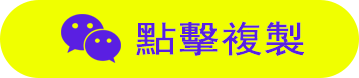




評論列表
挺專業的一個情感機構,我一個朋友在那裡諮詢過,服務很貼心!
如果發信息不回,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