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作家協會主管【貴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貴州作家創作成果、關注文學新人、多視角反映貴州文學生態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641
貴州作家·百花園地
嚴小妖的詩
嚴小妖:1989年生,貴州人,金牛座,喜歡紫色,著有詩集《前面後面都好》。

省油的燈
你想見我
我就在
你不想見我
我就遠遠的在
孤獨
小妖在河邊
洗孤獨
白花花的孤獨
很遙遠的地方
也有一個姑娘
在河邊洗孤獨
她洗得比小妖認真
孤獨也
比小妖的好看
講故事誰不會
戈多村的村尾
有一座御龍橋
傳說,這裡有一條
會吃小孩哭聲的大龍
每到夜裡
村裡的小孩一哭
大龍就會飛出去
把哭聲吃乾淨
把夜晚吃得
沒有一點多餘的聲音
老公的精子
小小
圓圓
細尾巴
白天羞答答
才入夜
就從淺白
到淺紅
再游到深紅之巔
我迫不及待
用手握住一顆
要哭了
這是未來兒子
好單純的
小模樣
對付出軌女人的辦法
荊棘藤條一直
住在她體內
只要她的身體和思想
不被別的男人打開
藤條就不會生長
總有狠心的男人出現
握住這根藤條
不但緊握不鬆手還
來回抽動
女人每走遠一步
他就拉這端的藤條一下
女人走不遠也回不去
就這樣反反覆覆
直到藤條被磨得光滑
直到女人血流不止
熊生嬋的詩
熊生嬋:2000年生於貴州水城,出版個人詩集《我是我,我是每一個》。作品散見《人民文學》《山花》《詩刊》《草堂》《大家》等刊。
途中
在山頂等待日暮
狂風清掃可疑的白
馬匹早已無人問津
想起一個人的有生之年
在這群山之巔活得認真
勝過褐馬黑馬白馬
風會把我們一個個吹得
鼓脹起來
像許多廉價塑料袋
安居街的流浪漢
一束艷麗的玫瑰
一隻白色的塑料袋
半袋水
一尾年邁的魚
魚在水裡吐出感嘆號
玫瑰花在長滿泥垢的手上
垂直生長
流浪漢除了這些還有一件
磨損的舊皮衣
除了舊皮衣還有一雙裂口的
舊皮鞋。除了舊皮鞋還有
用來審視周圍人群的漫漶眼神
這裡是安居街
有家可歸的人和無家可歸的人
並不屑於攀比
紅燈行綠燈停是人們耳熟能詳的
除了流浪漢總把斑馬線當地獄之門外
一切都很正常
魚在海里游泳
玫瑰在花圃里沐雨淋風
白色塑料袋
裝滿食物和幸福
冬日·一爐火
那個冬天的夜晚
我們圍着一爐火
滾燙的米酒
滾燙了全身
微醺的醉意
來自你盈盈眉眼處
仿佛窗外的雪花只是
作為陪襯而存在
火爐更旺了
你用手指敲打着
堅硬的栗子
你把白天透明的風雪
也一同融化在心裡
那些從未唱過的歌
也變得鮮活明亮
「就假裝她已死去
這是一場溫暖的葬禮」
你自顧自地笑和哭
圍坐在你周圍的親人
都像極了大刀長茅
都像極了寒風冷雨
直到女人血流不止
何瑤蘭的詩
何瑤蘭:1999年生,貴州德江人,土家族。現就讀於貴州民族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有作品散見《山花》《詩潮》《中國詩人》等刊。
小小詩
並不比雪白,比深冬夜裡將熄的爐火
輕。但它夠小,夠裝一粒塵埃
夠在塵埃里建築一隻小老虎
夠我騎虎下山,穿寂寞深林
與黑暗博弈(小易勝大)
我寫這樣小小的詩
並立志,成為你小小的人間
天亮了
她用紅毛線在脖子上纏了一圈
她用紅毛線在肩上纏了一圈
她用紅毛線在腰部也纏了一圈
她把自己纏得緊實又不乏柔軟
她說這件事發生在多年前的深夜
那時還沒有刀劍,沒有鮮榨機
沒有三隻公雞來換走她的女兒
她像往常一樣,以為睡一覺
天就亮了
米蟲
這是它舉起鐵盒子銀鐲子的第五天
乳白色的孤島不斷碰撞,沉沒
它打碎喉嚨,只是哽咽
一定,一定是更遠處的曠野
深處下起了大雪
這雪蓋住了整個世界
以至於讓它失了音
以至於一個邊緣人
失了音
值得
相公,來來來
這是上等紅雲一斗
選擇性春風白露盡,五兩
你可得小心記着
灑無解方程式揉和
切古城的白天與黑夜為片
相公,來來來,今夜有月
你且將牆角海棠花風乾
放竹篘着河流等候白馬
白馬上有青山數座,寺廟幾家
相公,你且一去不回,負心薄義
這人間吶,處處大雪,刀劍婆娑
菠蘿奶昔
這並不奇怪,鹽水還是得愛上
分解菠蘿時,樹林裡的陽光正好跌落
我看見她的頭髮大把大把地掉
撿起那些掉落的香氣時
仿佛正撿起一整個深沉的田野
仿佛她那些小荒謬和小絕情
還很是楚楚動人
王冬的詩
王冬:1995年生於貴州安順,寫詩、譯詩、作畫。
冬日頌歌
——記傷愈後一次長跑兼致友人艾非
我極少讚美日光,耀眼的影,
暴露在刺骨的寒風裡,有人與我擦肩。
在這一塊橙紅的圓形跑道,將疼痛
拋在了散落的頭髮後面,像狂奔的
野馬,陪伴在周圍,沒有親友的人們,
感到一種坦然的自由,我慶幸與其同行,
伴隨他們,就像認識了嶄新的植物,
曾經真實地觸摸過日光傾城的樹葉。
我們或許變得緩慢,但不曾停歇,
在寬闊的空間裡,製造相遇,新的交點,
眾人深重的喘息聲,掩蓋了你,
但挽救不了你。
極少的溫度,和交談。我清醒
在某個長滿青苔的角落,短暫的日光照射,
如米小的苔花開始綻放,
依舊如曾經被觀照過的命運,還有什麼?
能阻止它繼續生長,或許是
這久違的溫暖,融化了
無形的隔膜,消解了冬日裡
堅硬的冰霜,微弱的爆裂之音
你攤開自己,展現出狼狽、不堪。
我忘記並重建了新的回憶,在這無限循環的
樹影里,那些搖搖欲墜的葉子,與今冬和解於,
我頭上,一頂
純白毛絨帽子:新的庇護
霧中所見
——兼致健健
「大霧終將散去」,
是夢醒時記下的一句,
春分日過後,
煙草的幼苗,長出圓的葉片,
貪吃的倉鼠咬下一塊,
後來它就死了,有人開始哭了。
你在海洋頂端,而我被壓在海底
我們之間,隔着島嶼,
深海少女,吐泡泡依然是每日練習。
我墜落時,緊貼同類的殘骸,
倉鼠爸爸也有憂傷,是我未知曉的,
愛的本質,是痛苦的? 快樂偶爾浮現。
海底的溫度像冰,壓迫感,
像時空的裂傷,有時候嗅到鐵的氣味,
是一隻魚掉落的鱗。
它被人類發現,它對食物過於信任,
於是飛走,夢裡我看到它斷裂的身軀,
只剩下細長的尖刺。
建設
在我這兒,你安靜睡着,
冬日無暖陽,飯後疲倦感,
你的呼吸,輕而緩。
從燃燒的舊居回來,我記住了,
那烈火焚身的滋味,它在我身上留下印記,
似乎告訴我,屬於我的標誌。
過氧化氫,是溫和的,
我腿上吐出白色泡泡,
結痂時,一種愉悅的疼痛。
某一刻我像寒夜裡的燈?
把你照亮或者引你入迷途,
你將返時卻依戀,憧憬的真理。
你想要逃脫,卻抱緊我,
一個簡單句子,反覆敲擊心臟,
我們都受困於此。
我——一個年幼的造物者,
企圖在斷壁殘垣中建設,
還忘不掉純與潔的揪扯。
我叫綠
Ⅰ
那如此新鮮——
黃色外套,體內的溫度升高,輕輕滑入
一個赤裸着的男人撲來
手臂覆蓋着半濕的頭髮
他進入我自閉的小湖泊,像一棵蘆葦
進入我碧綠的草地,同我的呼吸聲一起進退
雨聲激烈,泉眼般涌動
窗簾拉上,風將它輕輕捲動,還有他——
屹立的小塔連接起我的皮膚
重塑我的形態,讓我變成女人
Ⅱ
那何其虛偽——
那季節已到來,那羽毛也降落
那到來的季節是消逝的盛夏
那降落的羽毛已踏遍各地
踏遍各地的,踏盡各地的也踏向我
踏向我的幻覺,我的清夢
而我輕薄,如一隻蟬翼
如一塊即將脫落的褐色枯枝,如一片綠葉子
除了野花,還有他——
仿佛我的存在就是為了襯托
讓他重新獲得讚美
他再次丟棄的,是林中的綠色的我
幻覺出現又消失
像一片青綠色葉子的枯萎
Ⅲ
緩緩地,流水從橋下西去
我坐在圓滑的大石頭上,我坐在夜色當中
唱讓人着迷的歌,在那裡我掏出真心
夜晚的露水,我展開的葉子
我慢慢地走出,不舍地
離開這讓我存在過的一束,那時:
野火灑落在我們之間,燃起它閃晃的光線
人群中,他
敘述着眾多踏過的葉子,但,你是誰?
你在那些衰老的葉子中間,是其中的一片
曾包裹着這被無數葉子包裹過的
當我枯竭時緩慢收攏,回到自閉的小湖泊中去
這自閉充滿警惕,充滿我——
但,我是誰? 我
失去的是綠色,那綠色是我——
在煤礦村
Ⅰ
太陽照進來時我已醒了,
我感到,一陣熱風撲面。
我剪掉玫瑰細小葉子和它的莖
要調一杯純正玫瑰奶茶
窗台下是鄰居的
房頂,平坦的。
廢棄的浴缸,種滿了花草。
在通往房頂的一角,
一棵茁壯的花樹,像薔薇科的。
鄰居有時上來澆水。
他是那樣溫柔,就像
為上學的小女兒梳洗
Ⅱ
傍晚時我回到這裡,
旭東路擠滿了車子。
戴着頭盔的人們就像瓢蟲,
站在綠色葉片上謹慎挪動。
沉溺於夜色中的人群,
總是等待着夜幕降臨。
而我獨自在樹下走,
走回山腰,路過那些燒烤攤。
和那間娛樂室——
嘈雜的聲響中。
有一種哀傷,
近乎流浪者的顛沛。
Ⅲ
亥時我已回到家中,
脫掉這沉重的外衣。
讓自己沉浸在,
浴室的白色水聲里。
而我在深谷的低端,
音樂聲讓我墜落。
一直在飄搖,仿佛我。
就在烈火中,在融化中呼喊。
受限於網狀的窗口,
有人在下面交談。
就像我對愛人的呼喚,
哪裡沒有不能癒合的傷口?
Ⅳ
是否一個人獨居太久,
就得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
人群,和酸澀的檸檬?
是不是她躲避城市的緣由。
當這些都消逝,
生活就變得空曠而甜蜜?
是不是我已脫離,
像一隻緩慢的蝸牛。
幾乎和外界隔離,
背負着沉重的軀殼。
我開始發現荒蕪,
就像山風和野草莓。
原始的森草味
和持久的梅雨。
反而給我將自己
都安全地保護起來的竊喜。
Ⅴ
我的一生短暫,
像一隻山雀的飛升。
我的心淡漠,
像一棵衰老的褐色枯枝。
我的快樂是一個詞句的浮現,
我的苦難是一口陳舊的深井。
驚醒於這山腰的村中,
打開燈光,思索着。
一兩聲雞鳴,我渴求天明,
就像昨夜渴求星辰。
蔣在的詩
蔣在:1994年9月生。詩歌見於《人民文學》《詩刊》《星星》《北京文學》等。小說見於《十月》《上海文學》《山花》《長江文藝》等,獲首屆《山花》年度小說新人獎。
生的時候只想着生
站起身
無限地焦慮
想着明日大雨隔斷
去機場的路
或是影響飛機的起落
該如何是好
天很暗
我問女主人
這雨在伊斯坦布爾常見嗎?
她說不常見
我看着外面的街道
有軌電車呼哧而過
我不能躺下身睡着
漫無邊際的早晨和黑夜
我不能痛苦而疲憊的醒着
好像生的時候只想着生
死的時候卻在想着別的事情
我為愛情說過的謊話
下午
三十二隻烏鴉同時起飛
給予我一天
等待焦躁隨時落下
背過身 站在他們身後
多少個不應該
看着他們落下吧
不該
在夜裡開燈
不該
在夜裡說話
我在想
曾為愛情說過的謊話
碰擊海港 碼頭
和岸牆
造成的傷害或是妨礙
用來 被我當做籌碼
預料 明日的雨天
一艘輪船
和另一個人在大霧裡相撞
午夜的計程車
他寫道
雪還有鷗鳥
成為代號或是編碼
那該是怎樣的冬天
又是怎樣的後悔
我躺在床上
不能閉眼
來生相見不再相識
他們看出破綻
不忍揭穿
不願想起我
為了送別
在暴風中提上鞋
我是沙丘和漁火
理應獲得另外恰當的沉默
早禱
每天盤旋
回眸六次
仰頭看看
那上方的梁頭
有三道切口
若誰向你問起了我
你說你來過了沙漠
卻沒有找到我
每天盤旋
回眸六次
你不管朝向哪個面
你的臉
始終對着我
無論你站起
還是坐下
你若是見了
鵝毛般的大雪
解開你的長衫
你若聽見有人喊你
你別轉過頭來
把不幸和上帝
一同交給他
手中的白桂花
望着愛琴海
在灰褐色的海岸邊
為哨兵造一座
無人拜訪的丘墓
丘墓旁的白桂花
在富饒的雨水裡
換上一桶油罐
把臉洗了又洗
扣上
我自由的白桂花
白桂花的浮香
轉向天邊落日
曬成哨兵
手裡鐘塔的杏黃
堆成無人探問的莊稼
我用餘生將你拾起
掀開你夢境中
滑下的面紗
烏鴉落在了別家
我住的山頭 看不見雨雪
或者 來年
大雪封門
是誰扣開了 枝葉的間隙
你遠道而來
空無一物的思念
雪未化 花已開
茫茫草場突然的來訪
概述了我們將來不會存在的立場
陌生人
在山腳下
池塘里圈養的馬
他們不說話 我也不說話
一筒水酒
一坨鹽巴
一塊茶
烏鴉也落在了別家
芒草的詩
芒草:1995年生,貴州人。詩作散見《延河》《詩潮》《詩刊》《山花》《貴州作家》及年度《中國詩歌排行榜》《21世紀貴州詩歌檔案》《貴州90後詩選》等。
一個人
一個人進山,省掉投石,問路
再不會打草,驚蛇
月過津渡,霧罩清澗
一個人,生前過不去的坎
走到盡頭,就都過去了
季節凋零,一個人
在風口上眺望,泥土冷清
人間的子孫,像四處散開的落葉
抓不住的,終將割斷
生前的一切,除了靜謐的墳墓
她什麼也留不下
我想,除了冷,一無所有的墓地
她什麼也感受不到
一個人啊,走了,像黃昏
定居在黑色的寂靜里
買菜
傍晚五點,戴好圍巾出門
稀瀝瀝的水滴,從天空滑落
不過是一場雨
穿過廣場,在哈着熱氣的菜場,我好像
找回了生活的溫度
精心挑選食材,掃碼,付款
從什麼時候,不再討價還價
甚至連菜品單價都不過問
人群中來來往往,都擰着沸騰的夢
想到你,我更不該把豐盈過成貧瘠
比如中午的外賣,我還是身體空空
等會兒,你瞧,廚房裡會冒着熱氣
我想象着,親愛的你
坐在我身旁,然後,暮色一點一點的融進味蕾
睡前
廚房的已濃煙散盡,共飲的好友在歸途
剛才升騰的茶葉在杯中靜止
揉揉眼睛,睏倦再次提醒
走到鏡子前,看到自己身體輕薄
又比昨天老了一點
回望窗台,想起一個逝去的親人
一根頭髮無聲的掉了下來
事實上,我每天都要撿起,這些衰老的證據
它們也是,我不斷浪費掉的青春和美
空蕩蕩的感覺,就在臥室里
春風不釋懷,空歡喜。總是
一半浸着濕霧,一半浸着淚水
讀唐詩
「小荷才露尖尖角「,新生多好
比起豆蔻梢頭,二月的春風,草木瘋長
而你,緩慢,含羞
連袒露,都用一整個季節
誰家玉笛暗飛聲,塵外之音,時輕時快
你的舊霧,我的新雨,空山中一年年刻畫
新舊齒輪
我舉杯,碰碎一地的拘謹
相互凝視,清澈的眼神,天空開闊
我們的言語,略顯多餘
一個人的一生,是不斷換韻的過程
尤其,一個人遇見另一個人
春天還在遲疑
時節已至,春風尚遠
雪還在下,悲傷還在滯留
我們都希望,桃花初開,暖陽早醒
拍掉頭上厚厚的積雪,來一場新鮮的雨水
原諒這場意外
而空城,封城,滾燙的句子不再跳動
時間磨損着,一顆熱烈的心
諸多的焦慮,暫時無解
傷離別,悲舊事,都發生在其間
好似羽毛輕盈,美好,而不值一提
那樸素的花草,何時緩緩歸來
我們在等江水清澈,生活清澈
萬物明亮可愛
就像昨夜渴求星辰。
兒茶的詩
兒茶:原名張立,1998年生,貴州畢節人。現就讀於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廣播電視學專業,雅風詩社社員。
銅雀春深(組詩)
銅雀台
依舊是朝東的窗,朝雲暮雨
撥開風聲,剝開水聲
從窄瘦的廊橋望過去
南金鳳,北冰井,漳水長流
有江,有月,有靡靡之樂
晚來的東風,再打撈不出一扇像樣的煙火
而檐角停靠的鵲鳴
已經就着曹孟德的舊夢棲息了好幾回
銅雀樓,是一座空城
與勝負無關
赤壁音
時間的褶皺里納着一架箏
引赤壁為架,抽東風成弦
有江,有火,沒有月,箏音低沉
二十三弦,還少了小寒
與刀劍相比
一曲悲歌與一簇火苗更相得益彰
被點燃的
還有桅杆上搖晃的一抹白
沿着赤壁,燒進了歷史的脈絡
銅雀樓,已是歸途
那些風花雪月的故事
借來杜樊川一闕舊詞留白
銅雀春深
等來寒鴉三匝
等來杜康無味
等來銅雀樓一座,沒有二喬
再誤入一句「銅雀春深」
那些面目暖軟的紅牆
大概在等着一個春天孵化
南來北去,東風不再是那天的那一場
無需計謀,無需求借
春天已被篤定
便是上了鎖,風聲已經走漏
西窗月
總有一些,是先來到的,比如
從老屋爬出來的記憶
植入西窗
擱置在窗台上的月亮
被割了一個傷口
流淌出來的桂花香
一不小心就把夢鄉醃入了味
把所有的月光放在一起
折進影子
無關緊要,我可以進一步推測
我們是兩個,流放異鄉的人
劉安倩的詩
劉安倩:1995年生,貴州赫章人。喜歡文字,愛好閱讀。有詩作散見《貴州作家》《零度詩刊》《貴州90後詩選》等。
惡意
霧靄與大地 作了帶上金邊的分割線
在黎明
你的樓閣同時亮起了燈
那病懨懨的案台
垂下眼眸 連聲嘆息
你蜷縮在木板床的一角
不肯轉身
木地板被喝醉的酒瓶砸出了缺口
降落的時候 我嚇跑了你窗邊的黑色蜘蛛
我是落在你陽台的飛鳥
昨夜剛經歷了 來自大洋海岸的風暴
路過你的花園
我並無惡意
因為風的緣故
春夏秋冬 四季之中
我最愛第三者
不因秋天是收穫的信使
捎來麥浪金黃 與
瓜果飄香
不因秋天是爽朗的讚歌
歌頌天高雲淡 以及
清宇悠長
這純粹的歡喜
只因風的緣故
林間的秋風
沾染了農家的煙火氣
在一張一弛之間跳躍
熟透的核桃與板栗
借力秋風
只聽見簌簌的聲響
果實便騰開外殼 裸露在地表
林間的秋風
不止是單調地吹拂
吹來烏雲 吹來雨水
也帶來了天地的饋贈
扒開老松樹下微微鼓起的松茸
還未出頭的蘑菇
就看見了人間顏色
一茬秋雨過後
一茬路人就來
那些自然的饋贈
自然成為飯桌上的野餐
我踩着秋風
腳印也陷得深刻
踩着最純粹的鄉土
連熱愛也更為真實
我愛這勝過春朝的秋日
只因風的緣故
寫給新年
一場發端於另一物種的疾病
因人類的貪食而爆發
打開歷史捲軸
鼠疫、流感、非典……
人類文明總伴隨着陣痛
那些不幸的患病者
成為了鐫刻過往的煙塵
人類原本像無數次面對苦難一樣平靜
有人嘀咕:病毒和我無關
照舊歌舞昇平
積聚宴飲
照舊
死亡者、患病者、疑似病例……
鮮明可觀的數字 不斷攀升
連絕望,都變得肉眼可見
像利刃 刺痛了 千千萬萬個家庭
一切運轉的因子 紛紛停擺
所有近距離的觸碰 變為奢求
許多人放棄了春節團圓
連炙熱的愛情 都擱淺
很多人在祈禱:病毒千萬別找上我
於是出乎意料地
口罩成為了最佳年貨
病毒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蔓延
同時 伴隨着偷偷摸摸
有人不知不覺成為感染者
有人有意無意成為傳播者
有人膽戰心驚成為觀望者…
用上任何一個扣人心弦的詞彙都不為過
醫療、建設 成為最繁忙的行業
無數逆行者 以期用比病毒傳播更快的速度
將其攔截 最好是肅清
此時的城市與村鎮之間
人與人之間
以從未有過的痕跡 變得敞亮
新年伊始
所有的「平衡」
驀然喑啞
沉默便與喧囂較量
鮮血與失望化成土壤
澆灌出真理之花
奔跑者與夕陽
如果沒有這場意外
人們很少去思考春天
季節更替周而復始
很少有人說起生生不息
取消了一切聚集後
商場、影院、交通…被摁下暫停鍵
所有人被告知 請主動隔離
這次的牢騷滿腹
作用對象是一場空空
城市不再喧鬧
鄉村尤其冷清
無數次白天昏睡 夜晚失眠之後
我想去追趕夕陽
同時攬住 一抹黃昏
奔跑的迷人之處
在於可以隨時發生
從前奔跑
歡喜的時候思考歡喜
憤懣的時候思考憤懣
空白的時候思考空白
即使奔跑 依舊攬不住黃昏
於是
我用汗水寫下
歪歪扭扭的一行字
遠方有蛩音 事有所成
賀澤嵐的詩
賀澤嵐:1998年生,貴州惠水人。2019年開始習詩,偶有詩歌發表和獲獎。
十二月
你出生在十二月
北方的皚雪在夜裡失眠疼痛。沒有一劑藥
讓一個小鎮抹掉歷史的淚水
南方喬木失聰,寂靜處漏出的西風羞於
啟齒,從不談論憔悴的事物
十二月。你帶來的是你的氣息和一雙描述
不清的眼睛。哦,還有一本落難的書
字裡行間長滿苦澀的青苔
它們不斷地在夜晚與星星舉行婚禮
它們和你的親人有上萬次不成功的別離
它們在病床上歷盡悲歡
祈禱
整個晚上,她都在不停地被拯救
輸血。刺骨。滿臉淚痕
仿佛一條毒蛇從腳心鑽來,恣意妄為
醫生把星群藏進她眉心的秋水
用鐵鉗在她的肋骨里敲響碩大的紅玫瑰
然後取出泥濘,隱去上等毒汁
窗外。陰霾之下白霜冰涼
我雙手合十,只祈禱一個二十歲的月影
斜出一株苜蓿
豆莢
它一直在庭院裡保持禮讓
一株久病的豆莢。這場盛夏的隕落啊
東風已從它腹中搬出輕盈的歡愛
只有母親依舊像良醫一樣施肥。鬆土
澆以褶皺的信仰,灌以江畔洲月
拯救它命懸一線的英靈
直到黃昏開始枯萎,一群白鴿
掠過日光的空缺。在時間裡悄然老去
母親才起身返回自己的六月
在更遠處的天空,白雲,一退再退
從豆莢的眼睛望去
我失去了辨別的能力。只剩致意
困局
取幾味老中醫的叮囑
法半夏、桑白皮、膽南星
哦,還有默不作聲的羌活
要先打開身體,將疼痛搗碎
揉成一滴哀傷的民謠。再倒入
幾分陳年舊事,放一些輪迴進來
熬煮兩顆星辰。隱匿脫落
沉珂喧譁,一如被修剪的生活
恍惚間,我記起多年前
爺爺就在這個藥壺裡
陷入命運的困局
深深
潮汐先於人群中失去自己深藍色的形狀
我的月色,是一隻夢的蝴蝶
愛所賜予的深情,都是我的敵人。我用泣血
滋養的玫瑰半生
而你,億萬光年裡未曾謀面的陌生日色
從宿命里延伸出一場與我有關的靈魂賭博
以狼煙、以火焰、以迷狂、以風暴
霸占了我星雲密布的風水寶地
這多麼忐忑啊。仿佛我
為之應運而生的一方純色燭火懸而
生生不停
貴州青年女詩人的生命立場
作者:淳本
一直想給貴州九零後的女詩們說點什麼,因為我們都不是中國詩歌的局外人,我們一起在參與中國現代詩的歷程,是組成它的龐大基數。因為出於對詩歌真摯的愛,又仰仗年齡關係,才敢對她們有所臧否。
現代詩歌與舊體詩不一樣,由於它成詩的特殊性,使得寫作者對於年齡的依賴越來越小。但基於寫得越多越容易形成套路,越容易思維固化的特點,新鮮血液的加入,便猶如在一潭死水中放入了一群兇猛的魚,那種活性的激發,是這個詩壇最需要的東西。因此,年輕人的加入,一直倍受關注。我也特別喜歡看後生們的詩歌,特別是九零後,喜歡他們對語言的觸摸方式,喜歡他們在文字中不拘一格的想像與飛升。但對貴州這批剛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我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去年趙衛峰老師邀請我去貴陽參加了一個詩歌討論會,才知道有這麼多年輕人又形成了新的詩歌力量,在這條路上前行。這次,選擇這九位年輕女詩人作為談論對象,是想從她們的文本中找到我們彼此交流的方式,至於那些表面的榮耀,我並不看重。由於我也是個寫作者,而非評論家,只能從寫作經驗與閱讀經驗去說出我的看法。且無意對誰褒貶,當然也不會吝惜我的真情。
女詩人的詩,一直是組成中國現代詩這個群體最豐富多元,最靈活善變的因素。這些,我均在貴州這群女詩人身上看到了,其中有直率熱情的嚴小妖,有天賦靈性的熊生嬋,有頗具古典精神的何瑤蘭,有西風中長大的王冬、蔣在,有傳統抒情型的芒草、兒茶、劉安倩、賀澤蘭等等。阿多尼斯說:「詩人應該持守一種生命的立場、存在的立場」,而我也在這些女詩人身上,看到了她們特有「場」和「生命力」。
嚴小妖是89年生人,我將其歸為90後,皆因在貴州的女性詩人中,她有完全不同於80後那種溫吞的烈焰。選擇小妖,不是因為她身上的話題,而因為她的濃烈與純粹。我不喜歡為詩而詩(不懂小妖的人可能會這樣說。)但當你看到她的詩里那種特有的純情與執着,或者說是執拗,一定會改變之前的看法,為之所動。如「你想見我/我就在/你不想見我/我就遠遠的在」。(《省油的燈》)短短四行,卻昂揚而堅定。這種「在」,在詩里,是小妖式的愛,在詩壇里,是小妖的生命力。
小妖的詩一直輕而狠。輕是指詞語拿捏,狠是指情感。所以,她總給人來勢洶洶,自戀而多情之感。讀她的詩,就像看到一個顧影自盼,眉目傳情的小妖精,讓人喜愛又心生忌憚。之前說過女性詩歌正因為有了她更為豐富的樣貌,才會獨立於男性詩歌之外,否則,就會被淹沒。而小妖身上的這種生命力與存在感,是貴州青年女詩人不可或缺的力量。她的直爽與坦誠,也很打動我,她說:「孩子,母親,老公,愛情,短詩,情色,醉酒詩(我大多詩寫於酒後)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我吧。」她說一個人不可否定過去。我想,也許就是這種堅定的自我認知與自我肯定,使她詩歌呈現出一種特有的飛翔之勢,不管你喜不喜歡,小妖就是她自己,可一個人,為什麼非要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的呢?小妖是堅定的口語派,但她的詩並不口水,在內在邏輯的推動上把握得很到位。在語言上,她有一種強行突破的能力,這很難得,是一個人對詩語言獨有的領悟。小妖說她只有在詩歌面前才是隨性的,但我想說隨性是自我展示的態度,而不是寫作技巧,所以,要注意一下在詩歌面前,嚴謹和隨性,並不衝突。還有,很多女詩人不自覺地將詩歌歸於「自娛」,小妖也是其中之一,這種自我中心的書寫,有趣而多姿,但也要注意多層次的抒發。
第一次看到熊生嬋的詩,我很吃驚,這個兩千年生的孩子,絕對是貴州女詩最有可能性的將來之一。對於這種喜愛,我是不吝多言的。她對語言和生命的那種直覺,顯得奇異而有活力,並且充滿啟迪。
詩歌最有魅力的部分,正是語言使用時的意外,這在熊生嬋的詩里得到最好的呈現。她觀察事物的角度,對意象的組合,對事物的解構,均有自己的獨特性,而最關鍵,她有不同於自己年齡的冷靜。如果說一個未足二十的孩子具有天生的敏感,我們都不遑多論,但她卻很冷靜地在敘說,這很奇妙——這種奇妙充滿了透明和通透(並非成年人那種自以為是的通透)。她沒有一般女詩人向內的重述,或許是她還太年輕,沒有所謂的歷史可嘆息,所以她的眼光都是向外的。她新奇地看着這個世界,冷靜地觀察和呈現,語言充滿摩擦力和流動性,閃耀着幽藍的小火苗。比如她說「在山頂等待日暮,狂風清掃可疑的白」,這「可疑的白」是什麼?是人之初的純真,還是生活中最簡單的美好?讓人好奇的同時,這種語言還在語義上充滿着斷裂的餘味,溢出很多可聯想的物。而下一節關於「馬匹」「有生之年」以及「褐馬黑馬白馬」的說法,顯示了小女孩的知識面與重構能力,讓人聯想到公孫龍的「白馬論」,但熊生蟬並沒有簡單地將這種思想結果挪用,而是使用一個小技巧讓「白馬」等同於「褐馬黑馬」,揭露了事物的特殊性在生命的宏大面前,不值一提。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和作者的出發點是否一致,或許她只是靈光乍現,便迎了上去,是詩歌自己找到了她。而作為讀者,怎樣理解,那要就要看你如何調動你的有關記憶與累積。而一個小姑娘,能夠觸發到這些機關,着實是讓人感動驚嘆。她在用語言創造一個獨有的世界,而這個世界,也同時接納着更多的人。基於這一點,她的詩歌沉穩,有開放性,熟練而自在,不可多得。
當然,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處,何況一個如此年輕的詩者,她在充分展現自己的靈性之時,也會不小心露出一些不足的小問題,比如結尾處理時,怎樣讓氣口不往下掉,不要刻意地去戳穿,詩人怎樣讓位於詩歌本身,這都是該思考的問題。
何瑤蘭的詩充滿自足性,和女性意識中虛構的美感,這一點,讓她的詩奇詭而清涼。這在中國七零後的詩人身上有非常強烈的印跡,沒想到在九零後身上又重現。何瑤蘭在詩中,一直化身為另一個她,反覆吟唱、訴說,久而久之,便將這種人世薄涼變成了一種情懷,從某種意義說,這是傳統文化在詩人內心的折射。身在傳統文化這個巨大的「場」中,詩人所獲得與傳播的精神向度是不由自主的。作為一個女詩人,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是對抗還是交融,主要看你如何去認知。而中國更多的女詩人,都是選擇主動臣服(融合),然後再在其中找自己的位置,最終在詩歌里將這種恍兮惚兮的神秘感營造出來。是的,她們更熱衷於「營造」和「呈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對抗和揭露。何瑤蘭是這其間的繼承者,她找到了自己心靈交付的手段,這很好。我一直認為,現代詩不應該孤立於傳統,作為一個中國女性,應該有自身文化符號的反射點,當然,這很難一言蔽之。我終究也只是個詩歌寫作者和觀察者,而非評論家。就自己寫者經驗而言,如果擯棄與身俱來的文化經驗,其實是很難去重建另外的精神文化經驗的,以至於寫出的東西會不會成為另一種文化的延續,我藏着深深的疑問和警惕。而像何瑤蘭這樣的寫作者,將從舊體詩歌(或者文化)中得到的營養植於新詩中,形成新的生命體驗和寫作風格,既新鮮又熟悉。她的詩歌即是對世界的呈現,又是參與世界的一種方法,像是夢境,也像是囈語。她將女性內心天生的脆弱與灰色部分用這種搖晃的語調來打開,像是對自己說,也像是對別人說。正如她詩里「她用紅毛線在脖子上纏了一圈/她用紅毛線在肩上纏了一圈/她用紅毛線在腰部也纏了一圈/她把自己纏得緊實又不乏柔軟……」這不僅是詩歌里的「她」在纏繞,也是夢境裡的「她」在纏繞,她用詩歌將舊的自己在解構在消失,又重建另一個自己。而這種寫法,如果能提升到心靈更高的地方,對外部世界的反射更為廣泛和深刻,將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王冬的詩有着不同於其他女性詩歌的縱橫感,有深深的西方詩歌的印跡。我才知道,她原來是作翻譯的。第一次看她的詩就是在一個專門介紹西方詩歌的平台,叫「一朵花兒紅了」,當時就覺得這個作者的詩比較成熟。所謂耳濡目染,王冬應是深諳西方詩歌抒情敘事的傳統風格,在意象使用上,不是中國傳統的直覺和寫意,而是如龐德所說的「漩渦」般的集結和重疊,更重演繹和再現。她的詩,往往是很多意象累加的效果,讓人措手不及,或者說,讓人一時緩不過勁來。在語言上,則偏重於散文化,使得語氣上有拖長後的延伸感。因此,王冬的詩歌,意象密集,充分調動了五感,是知性認知與情感建構的外在「象」的呈現。這些手法使得王冬的詩像緩慢的水流,蘊含着無數可能性,同時又形成很多遮蔽,也形成更多停留,而這種停留又給讀者帶來了更多的思考與回味。這樣的敘述策略,相較來說比較糾纏。在目前口語盛行的情況下,會顯得有些有點獨立或是不同。在我來說,喜歡各種詩歌技巧的嘗試,認可綜合寫作為詩歌寫作的自然狀態,所以,我反而認為像王冬這種寫作方法不僅僅只依賴直覺而存在,更要求技術,是一種能力的體現。
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怎樣將技術變得更自在,出入無痕跡,所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我們融入其中,與天地為一體,方為快哉!
貴州青年女詩人中,蔣在可謂年少成名,詩歌小說都很有見樹。她的詩冷靜、自在、舒適,有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詩風簡明清晰,不拖沓的同時她也有着九零後特有的思緒比較游離的特點,讓詩語言充滿了不確定性。她的詩在敘述策略上從小說中吸取了養分,比如《生的時候只想着生》,作者將故事情節抽離成一個個鏡頭碎片,使得詩歌有了較強的畫面感,也就有了可延伸的去處,故事的張力也就此出現,留給讀者的空間很大。這種很現代和先鋒的寫法,也帶着典型的西風印跡,蔣在在注重情節呈現的同時,在技巧層面也有自己的心得。但是,用母語寫詩的語言意趣問題,我想,在技巧日臻成熟的時候,大家都應該多思考一下。
芒草的詩有着典型傳統女詩人的唯美、古典、雅致。將每個情節鋪敘到最豐富,讓詩歌在有序中呈現古典的意境之美,語言接近散文化,因此,整體詩歌會顯得輕鬆自足,這無疑是現代中國女詩人最擅長的。這種傳統同樣來自於古典文學的啟迪,傳統抒情詩的教誨。而這種典型的傳統女性內心也極其細膩敏感,傷春悲秋,「升騰的茶葉」「一根頭髮無聲的掉下來」都會讓詩人浮想聯翩,都會成為一首詩。而在技巧上用得更多的,是將傳統詩詞直接移植的這種本領,幾乎是這一類型女詩人最喜歡做的事情。「小荷才露尖尖角」「誰家玉笛暗飛聲」「月過津渡,霧罩清澗」,信手拈來,即能成詩。這樣的詩歌受眾較廣,這和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普及得較好有關,但這樣也容易將現代詩寫成古詩翻譯,這是大多數此類詩風的人容易落入的陷阱。所以,這一類詩歌風格的人最需要思考的是詩歌現代性這個問題,這也是大多數女詩人共同面對的問題。
包括兒茶在表達上也與芒草類似,劉安倩與賀澤嵐雖然沒有明顯古典語言的運用,卻沒有從傳統抒情詩的氛圍中走出來,僅停留在情感的表達與古詩詞意象的運用,而不是製造語言的橫斷面,讓現代性從中溢出。這和我們所受的教育有很大關係,也和我們對現代詩與中國傳統詩歌的銜接思考有關係。抒情是詩歌的基調,而這些女詩人都擁有着最細膩豐富的情感,紮實的文字功底,唯一需要的是去打通詩歌現代性與傳統之間那座神性的橋樑,去找到二者之間共同呼吸的「氣口」,這將是一項任重道遠的詩歌工程。我也相信,她們一定會找到最好的突破口。因為,她們是中國現代詩最大的一個類型群體,她們不僅是貴州,也是中國現代詩的未來,在延續傳統詩歌和文人精神的同時,獲取現代詩的新鮮密碼,或將成為中國現代詩最有可能性的一群開拓者。
當然,貴州九零以後的女詩人眾多,這幾人或許不足以代表,但卻大體展現了貴州女詩人在類型和風格上的豐富性。至於欠缺之處,這需要向國內外眾多好詩人多學習多思考,自己也要堅持多寫多練習方能達成。
以上皆為個見,不足之處,請諒解!
作者簡介
淳本:網名淡若春天,黔人。70後,居貴州凱里。出身書香,以為詩即是生活。
精彩回顧
歡迎關注
貴州作家
文學貴州
貴州文房三寶
貴州作家·微刊
以展示貴州作家創作成果、關注文學新人、多視角反映貴州文學生態為己任。
主管:貴州省作家協會
編輯:何沖 魏昉 蔡國雲
野老 老八 黃 勇
編輯部主任:黃山
主編:魏爾鍋
微信號:gzzjwx
投稿郵箱:gzzjwx@qq.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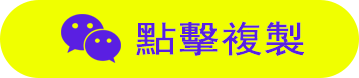




評論列表
確實不錯,挽回了不少瀕臨離婚的家庭!
可以幫助複合嗎?
發了正能量的信息了 還是不回怎麼辦呢?
老師,可以諮詢下嗎?